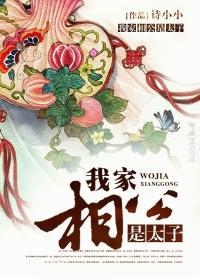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汉魏风骨的内涵 > 第十九章 主角(第3页)
第十九章 主角(第3页)
给我开门的佩刀狱吏也不管不问,倚在狱门边只跟着嬉笑,跟其他囚徒一块起哄,我登时发作,恶狠狠上前,正挥拳要给他点教训,却在想到自己目前身份那一刻停住了脚步。
“瞪什么瞪!臭娘们!当这诏狱是你家么?”
狱吏一掌将我推倒在地,险些将我面巾撞下,我隐忍着,赶忙将面部掩住。
“呵,原是个麻脸婆娘!难怪这粗活干得如此卖力!”
这话将我拉回数年前,顿时教我想起在南阳为奴为婢的痛苦经历,我也好像在暂时脱离权门贵女的身份后,突然清醒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
我不再言语,捂拳摁住鼻息,努力不使眼泪掉落,忍着屈辱继续推着粪车,执箕帚走进一间又一间监牢。
胃里翻江倒海,无数次快要吐出酸水来,幸而一日未进水米,无甚可吐。
呵呵,崔缨啊崔缨,你也有今日,这些年过多了舒坦日子,也让你这个虚假的“贵族”尝尝封建底层穷苦人民的滋味吧!
清扫了一日,开锁的狱吏换了两班,我才将整座诏狱扫除了一遍,且终于来到最后一间禁牢。
狱吏不耐烦地打了打哈气,在手中盘寻着禁牢的钥匙。
我斜眼偷瞄那串发出“铛铛琅琅”的钥匙,暗暗记下禁牢开锁的钥匙模样。可禁牢四面是墙,外头根本看不清里头样貌。
狱吏乙露出个诡异的微笑,将门打开后,他边说边后退数步:“喏——进去吧。”
“小心些,这里头的家伙可不好惹!”狱吏甲在后面笑着提醒道。
心脏飞速跳动,我根本没把这狱吏的话放心上,只疾步踅入牢中。
牢中漆黑一片,只有小块方窗顶上有片微弱的烛光。我摸索着踏入狱门那一刻,便敏锐地察觉到一声刺耳的锁链声。
手心直直冒汗,我又害怕又激动,只敢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终于走到墙根尽头了,幽暗中隐约看见一个披头散发打坐的背影——刹那间我停住了脚步。
“杨夙”二字,已经到了嘴边,为什么就说不出了呢。
还没看见那人转身,我已泪流满面,喉咙里像被灌注了铅水似的,喑哑无比。
四周静悄悄。
掀开面巾,双脚开始打颤,我拖着它们,努力往前迈开。
既然说不出话,那就朝他伸出手去吧。
可是,杨夙,见到我来,你会高兴吗?
我将右手搭在他右肩——
电闪雷鸣间,那人如触电般乍起,一个反手将我手臂扯过,用手中的铁链环套在我脖上,紧紧勒拽,令我瞬间头晕目眩,呼吸不得。
然后便是极其冰冷却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这肩,只有我朋友碰得,你怎么敢近前来的?”
我背对着他,看不清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快被他勒得窒息而死,却在听见“朋友”二字后清醒过来。
“我……就是……你的……朋友……啊……”
声音虽然轻微,拽链之人却显然身躯一震,力气渐渐放松,我趁机挣脱出来,伏在地上,大口喘起粗气。
等到终于缓过劲来,慢慢抬头,只见如此景象:
那人的腿没有断,只是有一条手腕般粗的铁链,自下及上,紧紧拘役着他的手和脚。单薄的素色衣袴,将手脚上的冻疮衬得愈发明晰!遍体可见的陈年旧伤,怎么数也数不清!特别是那双乌肿的赤脚,跟碎骨般瘫着,脚踝处还有巨大的疤痕!再往上,是一副瘦骨嶙峋的身躯,黑白相间的长发已蜷曲蓬乱,长须虬髯上面,是一张黝黑深凹的面庞。
那张脸,就是再添上一百刀伤痕我也认得。
眼泪瞬间就像断线珠玉似的掉落而下。
我只看了那双熟悉的眼睛一眼,面部便开始扭曲,我捂着嘴,极度的悲怆涌上心头,最终却消融为唇外一句颤声询问:
“杨夙……你到底怎么了?!”
我早心知肚明。
从我与他重逢那刻起,我的朋友,杨夙,将彻底取代我,成为这个乱世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