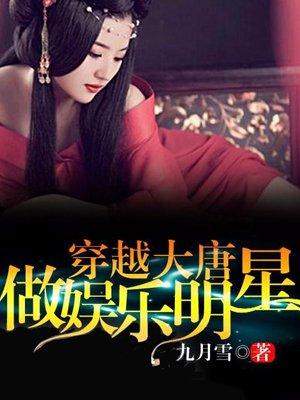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璇玑图多少首诗 > 第3章 闯入(第2页)
第3章 闯入(第2页)
崔繁露喘息不止,胸口匍匐,想说“多谢”,却发现自己的上下牙直打架。
“不用怕,我不是歹人。”黑衣女子从腰上取下令牌晃了晃:“我是大理寺评事柳凤染,闲来无事在瓦面溜溜,没想到在外面听到你呼喊,就进来看看。”
崔繁露努力喘匀气息,终于吐出了个“谢”字。
“不必客气。”柳凤染摆了摆手,四处观望了一下,道:“这是官邸啊,是你家?”
崔繁露点了点头:“嗯。”
“那这是你家的人?”柳凤染一脚踢向了地上那大个子的腰部,却如同踢在了一头死猪身上,毫无动静。
“不。。。。。。不认识。”
柳凤染不可思议的看着她:“不会吧?这不是你家吗?怎么还有你不认识的人?莫不是采花大盗?”
面对这么多问题,尚处在惊恐之中崔繁露完全无法招架,只得摇了摇头。
柳凤染动手在那大块头身上摸来摸去,只在腰间得了一块玉髓。她拿起来对着火光看了看,笑了:“邹?邹光昌家里的人啊。天助我也,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好不费功夫。”
崔繁露站起身来,双腿还有些发颤。
“你说你,行不行啊,弱柳扶风的。”柳凤染伸手搀她:“我看你刚才还拿着大针,是准备杀他还是准备自杀?这会儿怎么反而不中用了?”
崔繁露微微屈膝行礼:“大人稍待,我去换件衣服。”
说罢,便转身回到屋子里关上了门。
柳凤染将院子四处打量一遍,又打着火链照了照院门,对屋内的崔繁露道:“哎,那娘子,拿一盏灯来。”
房门再开,崔繁露素白襦裙,素白披帛,头发也利落的挽起,只在头上别一枚梨花簪,手提灯笼站在门边,在月光和灯笼淡橘色烛光的掩映下,更显得俏丽动人。
柳凤染看的呆了呆,心道难怪人都说灯下看美人。和她比起来,自己就像从煤球成了精,不仅衣服是黑的,常年在外奔走,舞刀弄剑,手指粗糙老茧横生,脸也是黑不溜秋的。
“你可真白。”她由衷的赞叹道。
“谢大人,”崔繁露将灯笼递了过去,又拜了拜:“先夫守孝未满,我来到这里也不过一日,未曾置办别的衣物,所以只能穿这身了,自知失礼,万望赎罪。”
“不怪,不怪。”柳凤染摆着手:“好看着呢。也就你能压得住这白衣,我从来都不敢穿白,显得更黑了。”
她说话直来直去,是个爽利的性子,言语间毫无遮拦,惹得崔繁露笑了出来。
那柳凤染提着灯笼,来来回回的查看了入院门的路,又看了看那淫贼的脚底,一只手摸着下巴捉摸道:“不对啊,这歹人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好似是从院门大摇大摆的走进来的。”
崔繁露深吸一口气,心中已经有了结论,看来真的是那王氏摆明了要害她。不过这手段也太过拙劣了,枉她还是王氏出身的勋贵娘子,下手竟然这等龌龊。
“你方才说,你才来了一日?你是崔家的人吗?”柳凤染问,显然是对她的身份有几分怀疑。
“是才一日,”崔繁露道:“我叫崔繁露,是奉议郎崔守一的女儿,不过之前一直住在清河县,今日才来投亲。”
“奉议朗的娘子姓王,这么说来,你不是正房所出吧。”
崔繁露点了点头,这才想起柳凤染之前的话,问道:“娘子可是说过,这贼人姓邹?”
“如假包换,”柳凤染扬了扬手中的那块玉佩:“这是邹氏子弟才有的玉佩,上面还有他们家族徽呢,你看这里,有个类似八卦阴阳鱼的纹路。”
崔繁露借着月光观瞧,果然如此。看来是王氏和邹夫人定的计策,只是这人是谁呢?
柳凤染同样迷惑:“不过这人和邹光昌什么关系,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也是刚来这长安城不久,闲来无事四处逛逛,没想到在坊外听见有人喊救命,我就进来了。”
“亏得大人相救,否则我今日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你这人好生客道,左一个谢礼右一声‘大人’,既然我一出门就遇上了你这庄子事儿,算是你我有缘,你叫崔繁露不是?我叫你繁露,你叫我凤染就行了。”
崔繁露点了点头,含笑道:“凤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