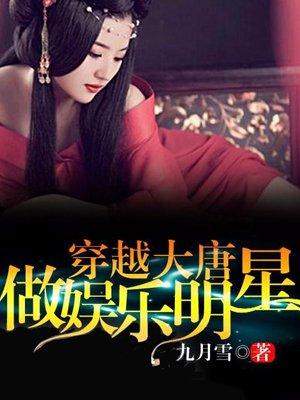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平行时空的恋爱综艺 > 第188章 遥望(第1页)
第188章 遥望(第1页)
“雅雅,是我不好,”doctorchong诚挚而理智的说,“我是真心想请他参与肿瘤相关的课题,谁知气晕了头和他吵了起来,我承认我脾气不够好才弄巧成拙,不过我依然看好他,我不会放弃说服他的任何一点可能,雅雅,就算我们都不提,你也应该很清楚你的病还未痊愈,你断了一年多的药,又拒绝任何关于脑部的检查,我很害怕,我怕有一天。。。。。。”
后面的话尚未说出口,赵清雅却比谁都清楚他指的是什么,苍白的脸颊上闪过一缕恐慌。双目被风雪冰冻,有凄清的寒意,桌上的手机又开始不停的震动,那熟悉的号码,灼伤了她美丽的眼睛。
钟往窗口一望,怔住片刻,自顾自说道,“好吧,你不肯见他,我就去替你见他,我们三个人,总有一个人要做和事佬吧。”
她不愿再多说,看着手中的杯子静默的垂下眼帘。
doctorchong苦笑摇头,汲拉着人字拖鞋,开门下了口。
宿舍下的玉兰花已经开得玉雪可爱,一树一树紫红色的花朵,有优雅的枝条,树下的男子背对着他,失神的拿着电话默默的伫立在原地,像是停留在严冬,被深重的冰雪凝固。
钟看他半晌,忽然觉得好笑,上前拍拍他的肩,好似一个老朋友打招呼道,“温医师,不上去坐坐?”
他沉默了半晌,眉眼不曾牵动,缓缓开口:“算了,没有这个必要。”
“怎么没有这个必要呢,”他恢复顽劣的本性,“你不是一直想贱内下来跟你谈一谈呢?怎么我这个愚夫亲自下来请你也不给面子?像你这么孤傲的人啊,不敢想象你老了之后会怎么办。”
他被他轻浮的言语说的脸色一黑,却始终没有低下他高傲的下巴。
白如羊脂玉的椅子上也净是玉兰花瓣,doctorchong随便拂拂,一屁股坐下翘起二郎腿,不住的抖动,“或许你过几天来更好,雅雅记性很差的,很快就会把一些负面情绪忘得一干二净,包括你说的那些不是人说的浑话。”
“无所谓,”他放下电话,漠然的说,“她爱怎么生气都没关系,就如你所说,她记性很差,你大可以继续兴风作浪,挑拨离间,也是,外人和亲夫,到底是有区别的,你没来之前她是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的。”
“看来你还是很介意我的存在,”doctorchong停止抖腿,凝重的看着他,“羡慕嫉妒恨么,如果你见过七年前的她你就会明白,我对她意味着什么,或许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衬托你而已,你现在骂我不要紧,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
他怒目而视,半晌才冷笑一声,“感谢你?感谢你趁虚而入?还是感谢你曾经禁锢她七年?”
他早已认定了他是个该死的插足者,钟无从解释,也不知道该不该解释。
“我都听说了,”他继续说,“你将她捆起来打针吃药,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这难道不算禁锢吗?更何况,你的心,并不止容纳着她一个人。”
“温医师,你真的了解雅雅在美国的经历么?”他加重了声音,“或许我可以告诉一些真实的情况。”
“不必,”温庭远正色道,“我会亲自问她的,请你让她下来。”
钟拿出手机拨下了电话号码,趁着响铃的间隙,他对他说,“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她提及你,没想到你的形象比她描述得更加生动。”
他冷冷的侧脸,不屑而怀疑的嗤笑,“是么?”
“是的,”钟凝视温庭远,笑容暧昧而意味深长:“一个比我聪明,比我英俊,比我更能给予她希望的,有别于我等凡夫俗子的完美男神。”
那些莫名其妙的愤懑在心底轰然倾塌,她那幼稚的言论被钟这样说出来明明略带喜感,却在七年之后的今天令他眼眶酸痛,他怔住,内心翻江倒海,那个冷冰冰被摔倒在地上的天使蛋糕渐渐浮现在他眼前,多年来不曾遗忘的手艺,他终于体会到她内心那一刻的失落与伤痛。
你是疯了么?明明决定要珍惜从千里之外回家的她。
你若不是疯了,又怎么舍得对她说出如此残酷绝情的话来。
钟凝视着他脸上细微的表情,轻声低语寥寥数句,镇定自若的结束了手机通话,“她不肯下来。”
他催促,“再打一次,就说我想见她,请她下来。”
钟苦笑着摇摇头,“她说她再也不想见你,你是王……”
后面半截他没有说出口,如果没有猜错,完整的话应该是,你是王八蛋混蛋卑鄙下流无耻的畜生。
钟笑完了对他说,“别跟她一般见识,这世上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
他眉头一皱,垂下眼帘,“算了,不必勉强了,我改天再来。”
“温医师,”钟叫住他:“要么跟我们一起去美国,要么别再见她了,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有没有我都一样。”
“如果我不呢?”他反诘,眉眼阴冷,“你有什么资格编排我的生活?”
玉兰花一树一树的开放,他的身影被树影映衬得修长,紫红色的花瓣在空中轻盈优雅,落在他的肩头,唯美好似漫画。
钟负手,抬目,望向五楼,果然她倚在窗户边目送着他离开,姣好的侧影纹丝未动,只余头顶一行飞鸟掠过,卷曲的发丝随着风飘荡,看得他惊心动魄,这切断治疗换来的一头美丽长发,未曾想过值不值得,只是凭着内心的感觉去奔赴一场未知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