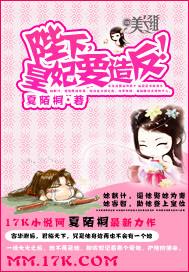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春意难违全文TXT > 61 第 61 章(第2页)
61 第 61 章(第2页)
俱远登时就慌了,毫不犹豫地转过身跪在了她面前:“女郎。”
钟引光知道此时绝不能表现出任何一点心软,板着脸继续吩咐:“不可废话耽误时辰。”
俱远急得差点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女郎,郎君不让告诉您实情,就是为了不想让您掺和进来,我没有欺瞒您,的确有些家事要他处理。”
钟引光心乱如麻,压根听不进去他说的话,遂猛地转过身,朝院中大跨步地走去:“好,若是你不打算替我备马,那我就自己走下去。”
“女郎!”俱远顾不上尊卑礼法,连滚带爬地死死抓住了她的衣裳下摆:“齐娘子为郎君病倒一事发了好大的火,说要是郎君胆敢再肆意妄为,便要家法处置,此时您实在不宜前去啊。”
狂风呼啸而过,没穿外披的钟引光承受不住这能令天寒地冻的一仗风,腿一软,差点跌在雪地里。
无尽用不容分说的力度抓紧了钟引光的手臂,把她往房中带,用几日来最严肃的语气说道:“女郎,您先回房添件衣裳,别的事容后再议。”
钟引光久久不能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双眼失神,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
无尽扶她坐下便又去拿外氅,他絮絮叨叨地劝了半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的,刚灌下一碗茶,就听见钟引光说:“去备马。”
喉间一哽,无尽差点呛着,他用袖子胡乱在嘴上擦了擦:“女郎,怎么还要去啊?”
钟引光维持着一副冷面:“九郎是为了我的事奔波才病倒的,若是连他病中我也龟缩在这,日后有何面目再去见他?”
无尽摆摆手,苦口婆心地说:“郎君哪里会怪您?现在掺杂着家事,齐娘子又正在气头上,您去了只会火上浇油。”
钟引光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只是系紧了刚披上身的厚实外氅,固执地说:“今天不论是你是告诉我轿辇坏了,还是马腿断了,我都要下山,休想拦我。”
这下连最后能用的借口都被她识破了,无尽好话歹话都说完了,但他拿打定主意的钟引光也没有办法,最终只能答应了下来。
风雪纷飞,落雪簌簌,钟引光有些日子没有到外面去了,所以她不知道山路上的积雪已经没过了脚踝。
她暗自骂了一声:离开家的时候自己忘记叫人带上鹿皮靴子了,收拾行李的侍女竟然也没想起来,现在踩在结了厚冰的地上,就好像踩在刀刃之上一样,双脚又冷又疼。
无尽知道她要回去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于是也不再磨蹭,快马加鞭地驱赶着马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疾速往上京城中赶。
天色擦黑时,钟引光一行赶到了上京城,眼前热闹的人间烟火一如往昔,种种景象都让在山中待了几天的她感到有些陌生。
恍惚分心了一瞬,她又很快收回了神思。
快要到齐府门口的时候,坐在外面驾车的俱远开口提醒她道:“女郎,一会见着郎君了。。。”
钟引光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但并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于是很快接上带过了:“你把事全部推到我头上就是了。”
俱远叹了口气:“女郎心善,我先谢过了。一会您先在门口稍候一会,我进去看看齐娘子在不在府上。若是遇不上她还好,遇上的话。。。毕竟去般若寺之前,她便已经发过一回火了,此刻见着您自己送上门来,不知要恼成什么样子。”
他说了一大段话,钟引光只从中捡出了最重要的一句:“来之前便发过火?”
俱远这下是彻底傻眼了:“您连这个也不知道?完了完了,郎君要是知道了我说漏了这么多事,不知道要怎么罚我了。”
钟引光没工夫听他废话,只是更加急切地问道:“临行前出了什么事?”
俱远一边叹着气一边回忆之前的事情,认真地同她讲:“临行前一天,郎君回到府中,突然说要借般若寺的钥匙一用,还说要上山小住些时日,却又对缘由绝口不提,可想而知自是被齐娘子拒绝了。”
“郎君去找了郎主,两人关起门说了足有一个时辰的话,期间连水都没让侍女进去加过一回,谁都不知道他二人谈了些什么。不过出来后,郎主便点头了,齐娘子无法,只得拿出了钥匙。”
钟引光在心中稍一思忖便明白了:齐意康没有向家里说出实情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着想,没有将此事告诉自己自然也是怕自己担心。
至于他和齐润说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女郎,女郎。”轿辇停下了,俱远愁眉苦脸地连唤了两声:“我可把什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