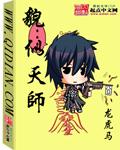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乱世烟华 > 第六十四章 男色倾城(第1页)
第六十四章 男色倾城(第1页)
“瑶山璧——父王以九座城池与州公易得,今次买你个丫头,够不够?”
暗哑低沉的嗓音响过,偌大的广场,瞬时鸦雀无声,整座钟离府的男女老少另加内宅外院全都卖掉,也没这个丫头值钱啊!
究竟是谁,连这个大脚丫头长得是圆是扁都没看清就丢出九座城池将其买下,简直败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噢,原来是扶楚,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看那狗仗人势的婆子,一扫先前的盛气凌人,此刻面色苍白,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接话。
再看进退维谷的郁琼,明显松了口气,甚至绽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挑高下巴静待姒嫣的反应。
未到跟前,密不透风的人墙就硬生生辟出一条三尺宽的过道,以供三边贸易中心有史以来出现的冤大头之最自由通行,还真是难为那些挤得不成人形的围观群众了。
扶楚闲适懒散,缓缓走到近前,就像先前的迟怀鉴,并不多在意自己高价竞来的‘货物’,眸子里浸满吊儿郎当,直直扫向仍端坐于上的姒嫣,心中一阵冷笑:这个女人若真的仅想要几个抬轿子的丫头,当初跟赫连翊言语一声便好,那个对自己女人向来出手大方的男人,待自己昭告天下要娶的王后,岂会吝啬?可这姒嫣竟装模作样,带着个趾高气扬的婆子出来炫耀财大气粗,只此一点,比起姒黛来,差得老远。
主事将扶楚请上台来,与姒嫣更进一步,听她娇声细语:“这价值九城的璧。到头来还不是翊哥哥的,他先时同我说。变卖钟离琇家业所得,尽数充作大婚时予我的用度,这一场,最后的赢家,终究还是我。”
胥追微微皱眉,看向扶楚,见她神色自若,才放下心来。
姒嫣此言一出,再掀哗然。在此主持大局的晏将有些发懵,上头只说这位娇客要好生款待,他却是不知,此女竟是未来王后。现在到底是该逢迎扶楚这大卖家。还是赶快去巴结未来王后呢?这个问题很棘手。
而那厢将将展露笑容的郁琼听了姒嫣的话,脸上又失了血色,目光渐露混沌。姒嫣还要落井下石:“有些女人,明明已是昨日黄花,拖家带口的,仍不安于室,镇日盯着别人的夫君,而今还要闹得沸沸扬扬。脸面何存?”
扶楚不必看也能想象得出,郁琼脸上该是何种颜色。可若无法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踏进这个赌局,便已输掉半数,虽郁琼今时大不同于往日,可她毕竟年轻气盛,扶楚摇头浅笑,不以为意,再出意外之举——天价竞买来的人,以人之常情,近在眼前,首先自当仔细查看,可她却是瞧都没瞧一眼,而面对姒黛的口出狂言,依着过去的性子,还不闹得个人仰马翻,可她居然表现得无动于衷,转身就去验货,看来三公子果真被人敲坏了脑壳子,做事如此毫无章法可循。
在女子中,扶楚已算是难得的高挑,差不多与寻常男子比肩,而眼前这个丫头,比她还要高出大半个头来,怪不得姒嫣要买她回去抬轿。
见她走近,那丫头愈发惊慌失措,彷如被猎捕的小兽,引得扶楚解颐,举手抬足,将那纨绔的形容刻画的入木三分,目光轻佻将她打量,且伸出手去,从那婆子手中将这丫头的手夺过来,攥住的一瞬,忽觉异样,低头看去,那沁凉的一点,竟是枚蒙了尘的银白指环,正端端的套在这丫头的食指上。
扶楚倏地眯眼,认真端量这只戴着指环的手,表面污秽不堪,却细腻柔软,她仍记得这只手——芙幺的侄儿,帮过她和佑安一把,是啊,钟离府的家丁,沾着钟离的光,全被发配到南边瘴气最重的地方去了,那是,有去没回;而和钟离琇沾亲带故的男丁,无论年龄,一概坑杀,芙幺的侄儿,就算是刚入府没多久,却也是男子,又和钟离琇沾着亲,难逃其咎,除非他是女儿身……
感觉到那只微微颤抖的手意欲挣脱她的牵制,扶楚微微侧头眄视他,嘴角噙着戏谑的笑,说出镌刻在他心头一辈子,重之又重的一段话,她同他说:“莫怕,你是本公子九座城池易来的人,从今而后,除了本公子之外,若有人敢动你一指头,本公子剁了他整只手,给你压惊!”这确然像个纨绔会说的话,却叫他瞬时愣住,忘了抽手,视线不再躲闪,直直望进她清澈的眼,如此放浪的言行,可她的眼却是纯净无痕,毫无亵玩。
扶楚也在看他,芙幺曾经说过,她一生中一共见过两双美得不真实的眼,一双是扶楚的,另外一双,便是她那侄儿的,这是双能夺人心魄的眼,琥珀色的眸子,蓄满小鹿般的仓惶和令人伤感的无助,那些仓惶和无助,绝非一日养成,经年累月,沉淀入骨,这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他始终躲在车帘后的原因吧,那不是深藏不露,仅因难安,扶楚略加手劲,将他攥得更紧,在这大庭广众下,抚慰着他。
感觉到他的手不再轻颤,扶楚转过头去,对那左右为难的晏将道:“文契呢?”
晏将没反应过来:“什么?”
姒嫣笑道:“还不把那丫头的卖身契给三公子送过去。”
晏将‘呀’了一声,忙翻出这丫头的卖身契来,向扶楚颠颠跑来,不等扶楚去接文契,那丫头身边的婆子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扶楚面前,头磕石板,咚咚的响:“婆子求三公子,将婆子一道买回去吧,婆子给三公子当牛做马,婆子的干女儿没有婆子,会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