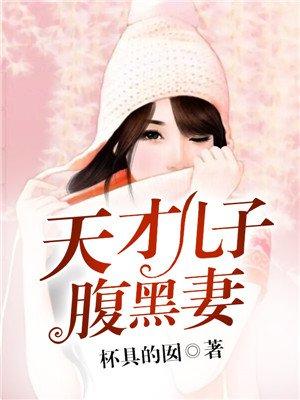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医妃空间文 > 第279章 我需要你相助(第1页)
第279章 我需要你相助(第1页)
谢渊北语气颓丧,完全没了往日在军中的意气风发,沉稳持重。
这也完全不像是他。
谢渊北是故意这么说的。
因为他知道,当今世上,若说还有什么值得白令俞惦念的,就只有两人之间那份难得的兄弟情义了。
白令俞总说自己孑然一身,孤身一人。
可当初谢渊北在军中也同他说过。
他们是手足兄弟,也同是家人。
看来这家伙是从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过。
思及此,谢渊北没由来的有些气愤。
不过并没有表露于面上。
依旧顾影自怜,自哀自叹。
好在,他没演多久。
床上原本了无生气的白令俞,突然有了反应。
先是瞳孔紧缩,紧接着干裂的嘴唇蠕动,喉间艰难的发出几个生涩的音节。
很模糊,寻常人便是竖起耳朵绞尽脑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但谢渊北听清了,也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别……死……”
晦涩的几个音节,像是腐朽的枯木破裂发出的刺耳声音。
但听在谢渊北耳中,却格外悦耳。
谢渊北攥着酒杯的手骤然收紧,双瞳发亮的转过头。
屋内一片静谧。
只剩下白令俞喉间、鼻间发出的越来越粗重急促的喘息声。
他如同困于笼中的困兽,正在为了自由奋死一搏。
身上单薄的衣物慢慢湿透,汗水一滴一滴埋入床单里。
白令俞脖子上,额头上,手背上都暴出青筋,每一根筋脉都狰狞,仿佛在不停叫嚣着。
他眼珠子都有些凸出,眼球上遍布红血丝。
不多时,从他喉咙里发出阵阵低沉的嘶吼声。
紧接着,整个人如同突然脱力一般,弓起的身子骤然落回原位。
床上一片狼藉,被褥和床单被拽的不成样子,隐隐有被撕裂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