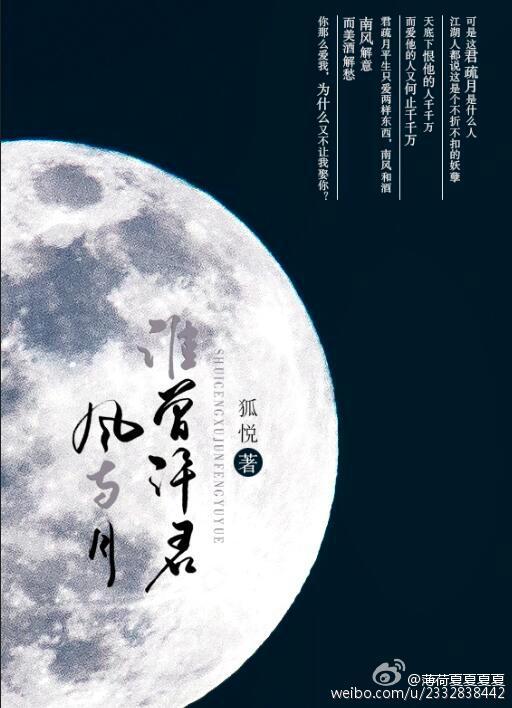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原谅你和你的无名指 你让我相信 还真有感情这么回事 > 第61章 同学少年都不贱(第1页)
第61章 同学少年都不贱(第1页)
房东的手始终是湿漉漉的,即使在粗麻布的围腰上擦了又擦,初春里晴暖的阳光照亮了她手心里的那枚钥匙,带着点淡淡的橘子皮的芳香。她总记得,曾经的他也最爱把钥匙放在装满橘子皮的陶瓷罐里,像一种风干了的古老的誓言。
房东依然不放心似地将手上的水珠子在衣服上蹭了蹭,然后才将那枚钥匙递到亦绾的手里说,“那天你走得实在匆忙,我倒糊涂了把钥匙还给你。其实这两年来,阮先生一直都有在交房租,偶尔会回来个一两次,匆匆忙忙间也就走了,只一次……”
那枚钥匙在银灰色的光芒里一闪一闪的,亦绾只觉得晃得眼睛疼,紧紧攥进手心里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的心在颤抖。她没有听清楚房东接下来说了些什么,只觉得耳朵里发出一阵阵血潮般“嗡嗡”地巨响,阮先生一直都有在交房租……偶尔会回来个一两次……匆匆忙忙间也就走了……只一次……房东的每一句话戳在心坎里就像是一把尖锐且磨人的刀子,她的手紧紧地攥住了胸口,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万箭攒心一般的酸楚和惊厥,原来,原来,他从来不曾离开过她半步,原来他一直都记得,可是……亦绾踉跄着扶紧了楼梯档口上的铁栏杆,她有短暂的眩晕症,偶尔犯起病来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她忽然感到害怕起来,害怕下一秒她就会从这个台阶上滚了下去。
钥匙插在锁孔里,而亦绾的手却始终是颤抖着的。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屋子里的一切摆设却都还是她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画面。
粉墙壁纸上贴满了他给她一笔一划写下来的嘘寒问暖的便利贴,亦绾,我听天气预报上说天冷了,要记得多穿一件毛衣……亦绾,我给你熬了点粥,早上别总是吃油条……亦绾,今天晚上我要赶论文,要不然教授可真要发飙了,记得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馆点点你爱吃的菜,不许吃方便面……太多太多,有的是糨糊都磨损了,稀稀疏疏地挂在墙头上,亦绾以前总嫌他婆婆妈妈,他说的,她只是敷衍似地点点头,所以,每次她出去上班的时候,回来就总是可以看见他的贴心的便利贴,一笔一划,精致婉转,像他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阳光从玻璃窗里泻进来,在屋里粗糙的地板上流转,一圈一圈晕黄的光芒,影影绰绰地照亮了书桌上那匣阮家明曾送给她的八音盒。那时,父亲刚去世,她走得急,除了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带走,甚至都没来得及和他道一声离别,雕镂着繁密花纹的八音盒上落满了时光的旧尘埃。
亦绾坐在床铺上,用手轻轻地拂去了上面的灰尘,阳光里,它们肆意地飞舞着。亦绾抠开铜环的时候,一层淡淡的铜绿染在了指尖,骤然间一股熟悉的旋律从音乐盒的低端响起,盒盖里镶嵌的一枚椭圆形的镜子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牵着个慈眉善目笑咧了嘴的老婆婆。那水晶似的人偶,那种天荒地老的不离不弃,随着悠扬的音乐欢快地旋转着,仿佛天地间惟有这种快乐,这种幸福是值得人伸出手去使劲地握一握。
她细细地摩挲着八音盒上的每一寸零件,那些曾经有过他抚触的温度,似乎还总是流转在指尖。阳光从窗帘的铜钩上斜倾了进来,映在了她手边的玻璃罐子上,蒙蒙的一层白雾,像隆冬时节北方玻璃窗子上结的几瓣霜花。
玻璃罐上系着一根粉红色的丝带,打着蝴蝶结的样式,很精致,像一出粉紫古装的越剧。亦绾擎开染着幽幽香气的木塞子,里面零零落落的塞着亦绾曾用彩纸叠过的幸运星和千纸鹤,粉的,红的,紫的,蓝的,映在了眼睛里,像一段不忍忘却的旧时光。
亦绾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千纸鹤的叠法是小时候父亲教他的,父亲喜欢用香烟盒里的银灰色的锡纸手把手地教着她,而她却总是调皮捣蛋地趴在小桌子上折起了小飞机,折好一个,就哈一口气,飞走一个,欢天喜地地拍着小手乐呵呵着,但最终还是在老爸的声声“小兔崽子”里学会了折纸鹤。
她看着它们,看着玻璃罐子里唯一一朵用信笺折成的粉红玫瑰花。初中时,她为了等到他寄过来的玫瑰信笺而永远也不会嫌累地每堂课下课的间隙就会跑一趟学校门口的传达室,惟一的期盼就是传达室的老师傅会招一招手对她说一声,喂,初二一班的萧亦绾同学,有你的信。那时的她,多傻,傻到以为一个转身就可以和心爱的他守到一个地老天荒出来。
等不到了,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过他是手心里握紧了的风筝,然而终究有一天风也会迷了她的眼,等到她揉亮了眼睛,猛然回转过身子的那一刻,她才发现,等不到的终究是要失去的,而如今她所害怕的,却是没有勇气再回过头来朝着来时的路毫无挂念地走一遍。
亦绾赶着去赴同学宴,她没有拆开那封粉红色的玫瑰花笺。不知是不愿意再度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还是心里始终存着一份不甘的执念,她将信笺和带着幽幽的橘子芳香味的那枚钥匙揣在了贴身的口袋里,那枚微合的玫瑰就开在了她的荷包里,带着凋零的喜悦。
不管怎么样,即使曾经她对他有过怎样不可原谅的入骨的恨,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愿意选择去慢慢原谅。自他带着宋绮珞飞走了以后,她曾对菲菲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至少他曾给过她一段最最美好灿烂的时光,在瓜渡村,在他的身边,就像一出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折子戏,他没有亏欠过她什么,彼此都是心甘情愿,她又何必死死抓住不放。
其实成年人的感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得失的计较,你给我几分我便要还给你几分,做不到飞蛾扑火。我们常常患得患失地算计着一份感情,却不知道爱情早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以前亦绾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谈钱,伤感情”,而在相隔了两年的大学同学聚会上,她听到的最多的抱怨却是”谈感情,伤钱。”
同学中不乏有的考上了公务员进了政府机关部门拿着稳定的工资和各种优厚的福利待遇,有的考上研究生的同学申请到了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的名额,有的混的风生水起自己投资创业当上了小老板,有的则混的是灰头鼠脸的,却硬是要打肿脸充胖子,西装革履的却难掩眼里的疲惫和焦虑的神色,而让亦绾最最吃惊的却是曾经和自己一个宿舍睡在自己下铺的苏茵,她和亦绾一样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姑娘,亦绾至今都还记得大学时她和阮家明在一起的时候晚上查房不能赶回宿舍的时候,一直都是苏茵想办法帮她瞒天过海,父亲生病住院时来不及请假的时候,是苏茵帮她向辅导员递的请假条。
在大学里,同学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微妙的变化,有的曾经好的恨不得拿双面胶粘起来的女孩子到头来却为了同时喜欢上的男孩子而反目成仇,有的穷人家的孩子为了争到班级里仅有的几个助学金的名额而背地里耍小心眼子。但是这风起云涌的四年大学时光里亦绾和苏茵之间却一直都像闺蜜一样无话不谈。
有句古话说过,“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女孩子的心智成熟比男孩子更早一些,因为苏茵是家里的老大,底下又有两个妹妹,农村里的上一辈们多多少少都会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虽然苏茵的母亲第四胎生下的是一个男孩,但也因为难产失血过多而早早抛下了这一大家子的老老小小们。
虽然说家里时常穷得都揭不开锅,但苏茵的父亲却是个望女成凤的庄稼人。再苦再累他都会供儿女们继续完成学业,但苏茵每次看着父亲瘦弱的身体拉着沉重的板车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地掉眼泪。苏茵的成绩从小到大都非常好,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她从学校里得回来的奖状,但看着父亲日益衰老的脸庞,初中刚毕业的时候,苏茵就决定放弃学业出去打工让弟弟妹妹们可以过上一些好一点的日子。
她瞒着父亲没有去A市一中报名而是直接去了服装厂去当缝纫工,虽然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加班到十二点,但厂里效益好的时候,苏茵却也可以多的点报酬。后来苏爸爸还是知道了,他只是站在女儿的身边,像一棵大树一般守护着深爱着的女儿,父亲没有说话,苏茵知道父亲一向不善言辞,但她却在仰头的一瞬间看到父亲眼角闪过的泪花,她的心忽然就微微地酸疼了起来。
她看着父亲摇摇头蹒跚着离开的背影时,眼泪忽然如狂风骤雨一般刷刷地就挂了一脸。
她知道,她不该让父亲失望,她知道,从来都不善言辞的父亲,却是用着一种深沉的爱来爱着她,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是世上任何一种感情也及不上的。
后来上大学以后,苏茵每年从学校里得到的国家励志奖学金都会一分不少的寄回家,三个弟弟妹妹,上高中的上高中,上初中的上初中,到底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好在弟弟妹妹们都非常懂事,学习成绩也都非常好,苏茵常常说,人只会苦一阵子,哪里会苦一辈子。虽然是笑着说出来的,亦绾却看到了她眼里的那种和自己曾经一样的无奈的心酸,她们都是坚强的女孩子,都是值得深深去爱着的。
亦绾本来以为成绩在学校数一数二的苏茵会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但再次在同学宴席上看到苏茵时她却已经是一岁孩子她妈了。亦绾没有想到她会一毕业就选择了结婚,或许太多人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只是她的婚宴亦绾却遗憾没有参加。
苏茵还是那样一副非常朴素的打扮,却是天生的美人胚子,无须任何的点染便透露着一股幽幽的清香气息。她有些歉意地朝亦馆笑了笑,微微说道,”结婚也是仓促间才决定的,我也是没有想过我会这么早就放弃了自己当初的梦想,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东西,他对我很好很体贴,孩子也一直是我婆婆带着,我依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她忽然拉起亦馆的手,一脸幸福模样地说道,”亦嬉,你和家明之间也快了吧,那时我可是尽心尽力地为你们把风哦,结婚的时候可别忘了喊我哦。”六始才R竺丈者五袖曰t层仕当之肩占的王消B日瞎甲裂分档的与此俱翻”当之节占丢若偷节汀l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