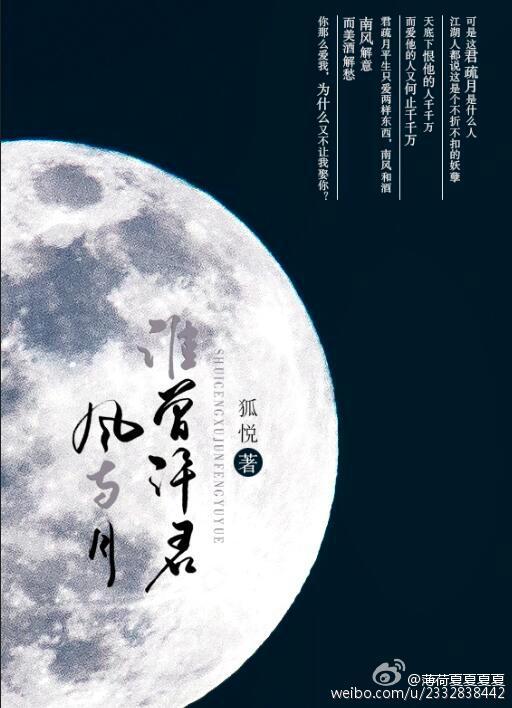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天命奇御2一拳定江山 > 第173章(第1页)
第173章(第1页)
&ldo;哀家收到铮儿的消息还少吗?&rdo;阮茵睁开眼,讥讽地道:&ldo;从铮儿起兵到现在,桩桩件件,你哪件事往仁寿宫少传了?&rdo;
&ldo;三哥是母后的亲子,儿臣怕母后惦记,才会多吩咐这么一句。&rdo;宁衍淡淡地道:&ldo;若是母后觉得心烦,儿臣以后不做这个恶人就是了。&rdo;
阮茵一噎,随即冷笑道:&ldo;铮儿起兵这事儿诸多疑虑,你当哀家不知道?&rdo;
&ldo;知道什么?&rdo;宁衍不动如山:&ldo;知道这么多年来,三哥一直在跟母后私下往来,从当初母后在皇寺时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未断了大逆不道的念想。还是知道三哥起兵,正是因为母后前些日子送去的一封信函?&rdo;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了,从宁铮起兵的那一刻起,阮茵和宁衍就同时踩上了一根细绳,在几十万兵马的对峙之下,最后谁赢,谁才能活着。
在这个大前提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道理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就算是阮茵现在承认什么,碍于宁铮的那乌泱泱几十万兵马,宁衍也不敢真就一杯毒酒毒死阮茵。
宁衍占据江山和&ldo;正统&rdo;,宁铮盘踞着这偌大江山中最富庶的那片土地,谁输谁赢还未可知。
&ldo;铮儿一向听话,若他真的收到了哀家的信,怎么会贸然起兵。定是你拦下了那封信,又做了什么手脚。&rdo;阮茵冷声说:&ldo;不然的话,哀家想来想去,除了那封信未到他手里之外,都想不出第二个可能。&rdo;
&ldo;母后可是冤枉朕了。&rdo;宁衍偏过头去看着阮茵,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扶手,神情轻松地说:&ldo;虽然朕在母后这里,向来没什么好名声,但唯有这一件事,朕还是想分辨两句‐‐母后放出的鸢可是好端端的飞出了宫城,到了三哥手里。&rdo;
&ldo;不可能。&rdo;阮茵断言道:&ldo;若是如此,铮儿绝不可能不听我的话,私自出兵。&rdo;
&ldo;母后怎么这么笃定三哥不是听了你的话,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rdo;宁衍意有所指地说:&ldo;毕竟三哥一直都孝顺得很。&rdo;
阮茵没有被他三言两语说得动怒,而是锁紧了眉头,探寻一般地望着宁衍。
宁衍双手搁在扶手上,大咧咧地任她看,端的是坦坦荡荡,无虚无畏。
&ldo;你‐‐&rdo;阮茵骤然想到一个可能,惊道:&ldo;你难不成换哀家的信件?&rdo;
&ldo;不可能。&rdo;阮茵紧接着就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恶狠狠地盯着宁衍,说出来的话也不知道是给他听的,还是给自己听的:&ldo;那晚哀家给铮儿传信的时候,从写信开始就都是亲力亲为,哪怕‐‐&rdo;
阮茵说得太急,一口气没上来,呛咳了一声。
&ldo;咳……哪怕是玲珑,哀家也没让她沾手半分。&rdo;阮茵说:&ldo;她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你当哀家真的那么相信她?&rdo;
&ldo;母后信不信玲珑不好说。&rdo;宁衍说:&ldo;但母后是开始信朕了。&rdo;
阮茵紧接着一愣,才发现她已经不知不觉走进了宁衍的话里,开始认真思索那一夜传信时究竟有没有疏漏了。
‐‐欲盖弥彰吗,阮茵想。
可故布疑阵这种小儿科,现在用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但就算如此,阮茵还是仔仔细细地重新回忆了一边,确信是自己亲手放进信筒的,这才轻轻松了口气。
&ldo;陛下倒也不必在哀家这里说这些。&rdo;阮茵说:&ldo;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rdo;
&ldo;母后这就是还不相信我。&rdo;宁衍故作遗憾地在袖袋里掏了掏,将先前给宁怀瑾看过的那枚竹筒掏出来,然后取出里头的信件,在阮茵面前慢慢展开。
&ldo;母后看看。&rdo;宁衍温和地说:&ldo;这是不是母后的字迹。&rdo;
阮茵本来就被宁衍这几句话弄得七上八下,看到这张字条后,终于绷不住那根脆弱的心弦,豁然站起身,厉声道:&ldo;不可能。&rdo;
&ldo;有什么不可能的?&rdo;宁衍反问道。
&ldo;那天晚上,事事都是哀家亲力亲为,哪怕是放飞的鸢,也是哀家亲自也检查了好几遍。&rdo;阮茵说:&ldo;根本没‐‐&rdo;
她话说到这里,忽然突兀地停顿了一瞬,
&ldo;哦……&rdo;宁衍了然道:&ldo;看来母后是想起来了。&rdo;
阮茵面上的表情变了几变,她看着宁衍,脸上满是惊疑不定,活像是见了鬼。
因为她忽然想起来,当时确实还有别人碰过那只鸢。
‐‐但也只是一瞬间而已。
那夜大雨倾盆,鸢焦躁得很,在阮茵往它足上系竹筒时扑腾了几下,尖利的爪子差点划伤阮茵的手。
当时阮茵谁也不相信,除了一个替她打伞的内侍之外,一应亲信都站得离她四五步远。
只是那内侍双手替阮茵撑着伞,一时倒不出手去控制那鸢,还好是一旁守门的一位小内侍冲过来,急忙拢住了那鸢的翅膀。
‐‐仅此而已。
阮茵下意识回忆了一下那小内侍的脸,却发现想不太起来。那人也在仁寿宫伺候了许多年了,总呆在侧门那一亩三分地底下,大多数时候都垂着头,跟这宫里千千万万的小内侍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