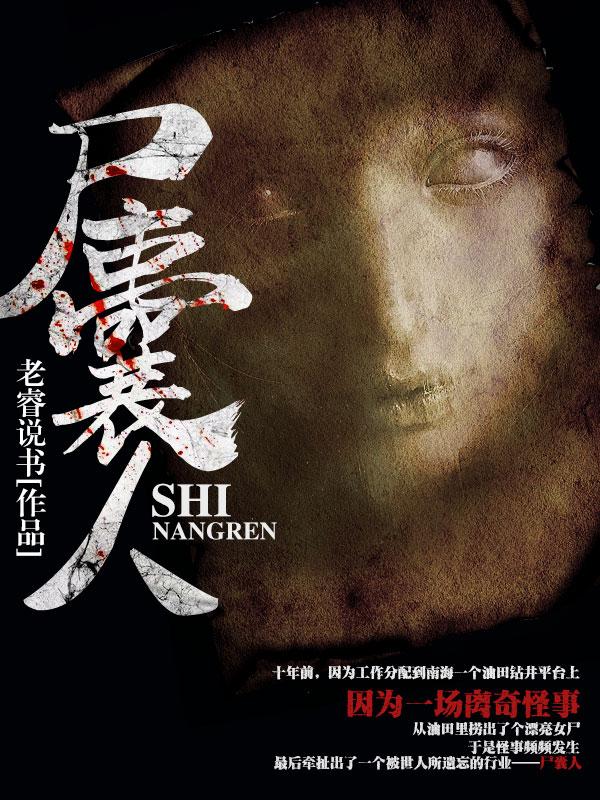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锦此一言免费全文阅读 > 第一百三十一章 表姐无辜(第2页)
第一百三十一章 表姐无辜(第2页)
刚一揭开纱帽,真吓她一跳!
只听她中毒,伤着脸了,可怎么个伤法伤到什么程度,没见着,这将将一露脸……真是!不忍睹……
难怪之前躲屋里不愿见人,谁也不让看。
这脸,还叫人脸吗?
“夫人,少安毋躁,待我问问再做打算。”
这人的脸,不是中毒,倒象是过敏。
很严重的过敏。
与表姐的有相似,但症状不同,显然不是同一种过敏源……
表姐除了脸,别的地方没有,不知这位……
“你除了脸,身上其他地方可还有类似红肿瘙痒处?”
“没有。”
平妻摇头否认。
锦言看她否认得迅速,不由怀疑:“你再想想,不把病状说清楚,会影响诊治。来,把身边服侍的叫一个进来,我有话要问。”
有人出去,不一会儿带了个丫头进来,锦言当着众人面,问了她事关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病状分布等的问题。
杂七杂八,全是日常琐事,各种类别的都有。
丫头很是茫然,数度去瞧主子的脸,可惜她主子脸上蒙层纱,看不出神情如何,得不到半分暗示,只得自己掂量着拣能说的说。
锦言挥手将人遣下去。
又叫了一个贴身服侍的进来,问了同样的问题。
这位同样茫然,也是选择按照自己理解的,拣分量轻重的来说。
这位又下去了。
平妻不乐意了:“侯夫人有事问妾身就是,丫头们不知深浅,哪里说得清楚。”
锦言微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饮食起居身边服侍的比本人更清楚,我知你有病心急不痛快,本夫人是在为你找病因……”
明摆着是心虚了,而且绝对有蹊跷,不然,问些生活琐事,怎么还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几个人就有几种说词?
又叫了一位进来。
反反复复将一二等的丫鬟、贴身的嬷嬷问了个遍。
这时旁听的也听出门道了——
侯夫人没问什么,无非是吃什么喝什么素日里喜欢做什么先头肚泻是怎么个情形,这之后的脸又是怎么出的症状,吃喝都经谁的手胭脂水粉用的谁家的……
没什么不能言的啊,怎么这些个丫鬟仆妇答得还不一样?
“……都是些小事,丫头们每日事多,记不清也在情理间。”
平妻跳出来为下属辩解。
这点事都记不住?这才几天功夫?
“……你待人倒是宽厚,这几个,是你身边可信的吧?”
锦言开始挖坑。
“不敢当侯夫人的夸,这几个是妾的陪嫁,服侍妾多年。”
平妻无所知。欣然跳坑。
“你这脸,是不是中毒暂且不论,但肯定与她无关。”
锦言指了指一直未曾言语的原配:“刚才你身边的人说得清楚。你的日常起居由她们几个负责,外人不曾假手。你又证明她们几个可信可靠。那她怎么下得了毒?此其一。”
“其二,刚才那几个虽说辞不一,但均表示她多日未与你会过面,时间最久的说是从去年初秋起,最短的那个说是自除夕之后,而你腹泻之症初起日距今十二日。她与你超过一个月无接触,又怎么能令你致病?”
锦言气定神闲。逐条掰开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