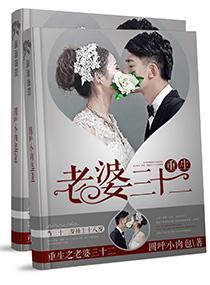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青春抛物线里面的手机是什么牌子 > 三(第1页)
三(第1页)
“大,我走了。www.Pinwenba.com”
南氏做好了早饭送到地里给父亲,他说他要去上学了,南氏父亲闷头在田地里为新种的麦田耙着垄,像大姑娘在细心梳着自己的发辫,南氏在说这句话时南氏父亲头也没有抬一下,闷声闷气地哼了一声,仿佛南氏不是在说一去几载的别离,而是说天上飞过一只麻雀。
“大,寒暑假我就不回了,我会很快地处理掉别人四年才能处理掉的学业,然后,我就可以挣钱了,我会带一大笔钱回来的,大,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你挡了我的耙子。”南氏的父亲说,他耙到了南氏脚下。
“大,您要保重,冬天的时候炕一定要烧暖了再睡,千万小心着您的老寒腿,锅里的剩饭,一定要热后再吃,别那么不在乎自己的胃,四季收耕会有我那些穿开裆裤时就建下了交情的村子里的兄弟们来帮,你就尽量地使他们好了,账我记在心里了……”
“你又挡了我的耙了。”南氏的父亲说,他的耙又到了南氏脚下。
“大,那我走了。”话一出口,南氏的眼眶鼻子还有心一同酸了,但是父亲还是头都没有抬。
南氏走着,一步三回头,田里的父亲一次也没有抬过头,但是第二天,他却拔掉了所有的番茄秧,把所有的鸡包括鸡槽鸡笼子都送人了,他说:“番茄是给南氏吃的,鸡也是给南氏吃的,那小子走了……”
秋天的乡间路,西风中每一步都能踏出一幕漫漫黄尘让眼睛一次次被迷住,很像很像不经意地触动却击落了记忆里一串又一串的泪水,让心一次又一次伤了。
每粒泥土都是大地的泪滴,它挂满在南氏的整个头颅、眉毛、睫毛、脸颊、嘴唇、下巴和全身。南氏带着它们走上了乡路尽头的公路,告别了黄尘幕幕,他转过身,朝着东边儿,太阳悬挂的地方走去。阳光的手伸进来,温情地抚摸着南氏的瞳孔,于是南氏眯起眼睛。
一辆雪白的汽车沿着阳光划来,如船破浪割开南氏眯起的视野,南氏睁开了眼睛—是吴得。
载上了南氏的车漂亮地打了一个旋儿,朝着阳光溯去。
“你眯着眼睛走在阳光里的样子,很酷很炫很有味道。”吴得说,“尤其是你那一身灰尘,太阳下面它们是金色的,闪闪发亮,像露珠沾满你身上,给你涂上了一层童话色彩。”
南氏望向窗外西风中北方剥去了金色的而倍显褴褛艰辛的大地,他的心随着它一道起伏波动。
“人一生最重要的责任是不是让生养了他的土地不再贫瘠?”南氏问。
“每个人对一生最重要的责任认识与其的成长背景有关,而每个人又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
“但是,有一句成语叫‘殊途同归’。”南氏说。
“是的,殊途同归,”吴得说,“一个让人充满向往的温暖的成语。”
汽车驶入北京,像一滴水汇入河流般,它汇入车流街海。
“不要给我写信,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更不要去看我,安安静静地等着我,我会很快的,我不会让你们,让你和我大等很久的,”南氏说,“吴得,你听清我说什么了吗?你要答应我。”
“我答应你。”
吴得先把车停在银行前,她带南氏到取款机前,交给他一张银行卡,示范给他看如何存款、取款种种。然后,南氏从衣兜里掏出来七千块钱,这是南氏父亲一生的积畜,是南氏考完大学那天早上,南氏父亲用布包了悄无声息放在南氏枕边的,多少天来南氏摸都不忍心摸,看都不忍心看,想都不忍想它,它是父亲几十年人生换来的。南氏把这钱存入了卡里,他感觉他把父亲的几十年、几万个日出日落里的人生跌宕存进去了,所以,他在取款机前站了许久,他不得不缅怀。
吴得把南氏带到了她曾经和父母居住、现在是她自己居住的地方,一所大学住宅区二楼的三室二厅。
吴得径直走进浴室,放水,调好水温,把一件雪白的衬衫,一条蓝色牛仔裤,一双雪白的袜子,一双黑色运动鞋,(牛仔裤上放着一条皮带)放在浴缸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