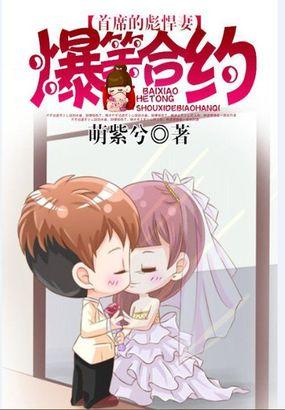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公府悔婚,我转身入皇家 > 第146章 你另外一只手也不要了(第1页)
第146章 你另外一只手也不要了(第1页)
事关立储之事,顺喜也不敢多说,只能低着头听着。
周惜朝素来为人仁善,此时不得不冷下心肠来,心里闷闷的有些难受,不免留着顺喜多说了几句。
“洛阳王进京之后,只怕端王要伤心了。”周惜朝说,他目光缓缓朝着窗外看了一眼,夜色暗沉,漆黑一片。
“若是父皇,也不知道会如何。”周惜朝苦笑了一声。
顺喜沉默了一下,一时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陛下和先皇的关系说不上多好,先是先是贬妻为妾,后又贬谪幼子,实在不能说是一个好父亲。
后来章怀太子病逝,周惜朝匆匆进京,父子俩相处了不到一个月,先皇也离世了。
顺喜敏锐的感觉道,这个新主子对先皇的感情很复杂,并不怎么愿意说起,这还是他十年来第一次主动提起先皇。
“奴才是个笨人,先前在先皇跟前伺候,旁的也没有学会,只知道一件事。”顺喜神情恭顺,面容和善的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做奴才的,只要各安本分,照做就是了。”
周惜朝瞧着他煞有介事的样子,一时间觉得又好笑又无奈,嗤笑了一声:“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会说话了。”
他伸手将被子往身上拉了一下,整个人都陷进了锦被里,看着顺喜,“父皇走的时候,见了阿云,当日你就在跟前伺候,可听到他们说了什么?”
顺喜迟疑了一下。
周惜朝大度的笑了笑:“你若是为难,便不必说。”
他的父亲临终之时并没有见他,而是见了霍云,既然当年没有见,他也不该去问的。
人生的路总是会向前,而他也总是摆出坚韧温和的样子一笑而过。
他是天子,万民之父,他从来不去回想自己的来时路。
顺喜道:“先皇同骠骑将军说了许多,奴才记性不好,旁的都不大记得了,只有一样,乃是奴才的本分,便记下了。”
“先皇说,这世上只有别人去迁就皇帝的,断没有道理委屈了皇帝去迁就别人的。”
周惜朝看了看他,觉得这话没头没脑的,但也听进去了几分。
他想起刚来京城的时候,为显新储君谦逊之德,他虽然被册立为太子,但却没有搬进东宫和端王母子抢屋子,而是住在东面的千波殿里。
千波殿离未央宫远,那时正是隆冬,他每日要起大早绕路去给父皇请安。
章怀太子新丧,天下缟素,为表哀思,宫中不许行车马轿辇,那一个月的早晨,他都要踏着积雪,步行很久去未央宫。
有一日天色赏早,白雪皑皑,他冒着风雪到未央宫,却见病中的父皇在抱月亭抱着端王,一边喝茶,一边逗沉默寡言的阿云说话。
他一身风雪,父皇难得的放下端王,扶他起来说话,彼时他已经手脚冻得冰凉。
“阿韶啊,做明君难,做私德无亏的明君更是难上加难,若事事想求完美,完美哪那么好求?”父皇看着他的面容,眼神里露出了长久的眷恋。
“天亮之后,册封县主的圣旨,要宣告给六宫。”周惜朝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朕要让所有人知道,朕对县主的看重。”
“奴才明白。”顺喜说。
“端王那里,你也要亲自去宣读,好来敲打敲打。”周惜朝冷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