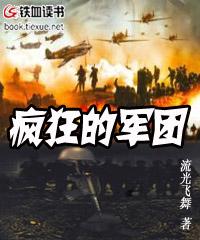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世界名人史 > 第64章 一休宗纯(第1页)
第64章 一休宗纯(第1页)
在日本室町时代的京都,夜幕深沉,皇宫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1394年,一休宗纯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降生了。他的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藤原氏温柔美丽且才情出众,本应享受着无尽的尊荣,可宫廷中权力的争斗如同汹涌的暗流,无情地将他们的生活卷入了漩涡。
不知从何时起,关于藤原氏图谋刺杀天皇的谣言如毒雾般在宫廷中弥漫开来。这毫无根据的指控,让藤原氏陷入了绝境。尽管她声泪俱下地辩解,却无法阻挡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恶意中伤。
在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一队全副武装的侍卫闯入了她的寝宫。藤原氏惊恐地抱紧怀中啼哭的一休,声音颤抖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冤枉的,我对天皇陛下绝无二心!”
侍卫头领面无表情地说:“奉天皇旨意,带你回宫问话,莫要反抗,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
藤原氏眼中满是绝望,她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看着怀中的一休,泪水止不住地流。她将一休托付给身边最信任的侍女,哽咽着说:“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孩子,带他去安全的地方。”
尚在襁褓中的一休,就这样被送到了京都安国寺。寺内的长老象外集鉴慈悲为怀,他望着这个命运坎坷的孩子,心中满是怜悯,决定将他收留。6岁那年,一休正式成为象外集鉴的弟子,并获赐名周建。从那以后,安国寺的晨钟暮鼓便伴随着一休的成长。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寺庙,一休就会在钟声的催促下起身。他熟练地拿起扫帚,开始清扫寺庙的庭院。
一同清扫的小僧人好奇地问:“周建,你说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做这些杂活呀?”
一休认真地回答:“清扫庭院也是修行的一部分,能让我们的心变得清净,更好地领悟佛法。”
扫完地后,他会来到佛堂,双手合十,虔诚地诵读经文。那些晦涩难懂的经文,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试图从中找寻到心灵的慰藉和人生的答案。
午后,是一休学习书法与佛法知识的时间。他坐在书桌前,手握毛笔,一笔一划地临摹着字帖。
长老象外集鉴在一旁看着,说道:“周建,书法如佛法,讲究的是心正笔正,不可浮躁。”
一休抬起头,恭敬地说:“弟子明白,定会用心练习,领悟其中的道理。”
时光荏苒,一休渐渐长大。13岁时,他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机遇——师从东山建仁寺僧人慕喆攀学习写汉诗。慕喆攀学识渊博,对一休十分赏识,不仅倾囊相授诗歌的格律与技巧,还经常带他游历京都的名胜古迹。
一次,他们来到长门宫。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阳光明媚,长门宫前的春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
慕喆攀看着眼前的景色,对一休说:“一休,眼前之景可有灵感?不妨赋诗一首。”
一休望着春草,沉思片刻后说道:“师父,弟子已有诗句,‘长门草色春常在,不见当年美人来’。”
慕喆攀听后,赞许地点点头:“好诗,好诗!短短两句,便将长门宫的兴衰与美人的消逝描绘得淋漓尽致,颇具韵味。”
从那以后,一休更加勤奋地创作,15岁时,他的诗作已经在京都诗坛声名远扬,许多文人雅士都以能与他交流诗歌为幸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休对佛法的追求愈发强烈。1415年,他有幸成为华叟门下的弟子。华叟的禅房布置简朴,却充满了宁静的氛围。在这里,一休与师父常常进行深入的佛法探讨。
一天,一休向华叟请教:“师父,何为真正的佛法?”
华叟微微一笑,反问:“你心中所认为的佛法又是什么?”
一休思索片刻后回答:“弟子以为,佛法是慈悲,是对世间万物的怜悯与关爱。”
华叟点头道:“这只是其一,佛法更是对自我内心的洞察,对世间真理的追寻,不可拘泥于表面。”
1418年,25岁的一休在一次外出时,偶然听到了盲人表演的平曲《只王失宠》。那悠扬而又哀伤的曲调,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一扇门。
他激动地跑回寺庙,见到华叟宗昙便说道:“师父,今日听到《只王失宠》,弟子联想到《云门放洞山三顿棒话》,似有所悟。”
华叟宗昙目光温和地看着他:“哦?说来听听,是何领悟?”
一休将自己的感悟详细阐述了一番,华叟宗昙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赐他法号“一休”,希望他能在佛法的道路上继续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