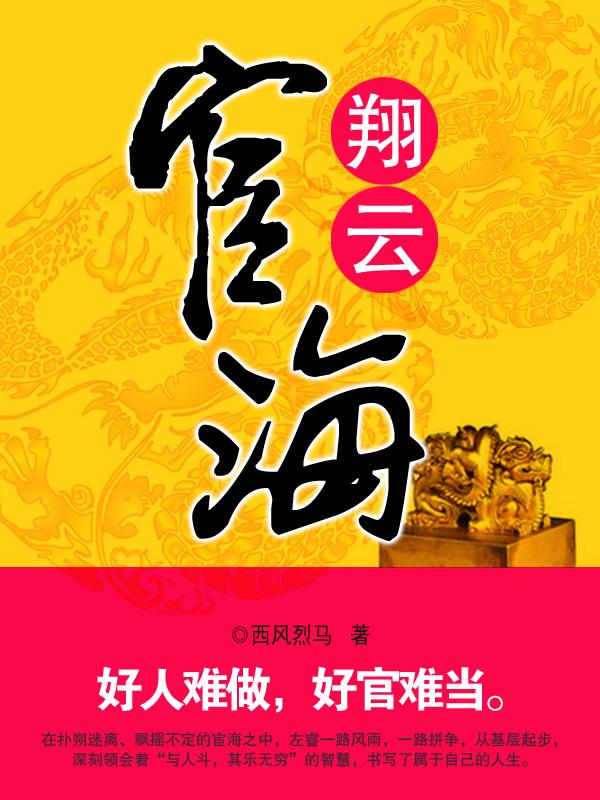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鸾凤劫:庶女成凰 > 第488章 全部奉还(第1页)
第488章 全部奉还(第1页)
这场猎杀的游戏,到了最后,到底谁胜谁负呢?胜的人还没有胜得彻彻底底,输的人也还没有输得心服口服。
直到走到牢房的尽头,转进了密不透风的石室,身后依稀还有凤时昭的笑骂声。
凤时锦在脚踏进石室的那一刻,迎面有湿腐血腥的气息袭来。她身形顿了顿,抬眼看去,见那木桩上正严严实实地绑着一个人,四面墙壁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刑具。那人穿着白色里衣,只是衣服上沾染了点点斑驳的血迹,耷拉着头很没有精神的样子。
明明是酷夏,那时凤时锦却觉得很冷,从脚心冷透到头皮。她以为自己回到了那个严寒的冬天,看见面前奄奄一息的男人。
已经很久,她都没再遇到这样似曾相识的画面了。她的脑海里也很久没有浮现出那日久天长的面孔了。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她犹清楚地记得,她在这里都没来得及好好地跟君千纪说上几句话,她见他浑身是血的时候,吓得六神无主,她见他受刑的时候,全盘崩溃。那么严酷的刑罚她都忍受下来了,但就是见不得君千纪受伤害。
她没能保护好他们的孩子,她很自责。君千纪也一样的自责,自责他没能保护好她。或许明明知道结果,还是要将她拉进来,贪图和她在一起的三年光阴。
他说她以后可以得到幸福,可以儿女绕膝,安享晚年。
直到此时此刻,凤时锦清楚,君千纪都是骗她的。她不会儿女绕膝,一生都不会再生育,也不会安享晚年,因为她作孽太多,还有幸福……她所有的幸福,都是被眼前之人生生夺走!
苏阴黎感受到生人的气息,抬起头来时,恰恰看见凤时锦眼里如深渊如地狱的冷光。
他最大的败笔,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凤时锦有机会活着。就好像当初苏徵勤最大的败笔就是让他活着一样。
人只要一活着,一旦心中有强烈的渴望,就算被逼到绝境,也能顽强地挺过来。
凤时锦就是眼下活生生的凤凰涅槃。
凤时锦越恨他,却表现得越平静。她站在苏阴黎的面前,与他对视。
凤时锦凉幽幽道:“总归还是,让你当了几天大晋的皇帝,你弑君杀弟的罪名会名扬史册,让后世的人都记得你,这也是你的一大收获。先如今你满盘皆输,别指望还会有人来救你。荣国侯么,他如今身在南方,成为叛贼乱党,应该已经自顾不暇了。你以前的那些党羽要么投诚要么死去,你也无人可依靠。”
苏阴黎沉沉粗喘道:“我真应该当初杀了你。”
凤时锦侧身睨着他,勾唇一笑道:“你最不该的不是没有杀了我,而是杀了不该杀的人。如此你便应该付出代价,用你至亲的鲜血,用你的天下来陪葬。”她拿了浸泡过盐水的鞭子,“当初,你在君千纪身上加了多少鞭子,现如今我一一还给你。”
她不用狱卒动手,她要亲自动手,一鞭一鞭笞在苏阴黎的身上,皆是用尽自己全身力气,打得苏阴黎皮开肉绽,白衣被染成了血红。
凤时锦一边打一边喘息着道:“新皇登基以后,你会被施以五马分尸之刑,你死后无全尸,你的身体会分别挂在城楼之上曝晒,死无葬身之地,永无超生之日。”
从大理寺出来的时候,阳光明亮得刺眼,照在凤时锦身上时,明明酷暑她还是觉得永无止境的寒冷。她身体打着颤,手臂因为用力过猛而颤巍巍的,苏阴黎身上的血溅在了她的下巴上,显得妖冶极了,衬得一张脸极其苍白。
苏徵勤蹙着眉,他担心下一刻凤时锦就会站不稳而倒下。他先一步揽住了她的腰,将她搂进怀,问:“可是不舒服?”
凤时锦双手抵着苏徵勤的胸膛,喘息久久不能平静,她半低着头,额头靠在苏徵勤的胸膛上,双肩微微起伏着,低低道:“我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苏徵勤扶着她的后背时发现她后背都已经汗湿了,冰冰冷的。他心疼道:“早知道,你让旁人打,你站在一旁看着不就是了。”
“不够……”凤时锦低低沙哑道,“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都觉得还给他们的,不及当年他们加注在我身上的千分之一……千纪、千纪他……也一定不会安息的,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狠……”
没想到凤时锦面对什么都异常冷静,却会在这天牢之外失控了。她茫然无措,在苏徵勤怀里极为不安,苏徵勤用力抱了她,手抚摸着她的头,哄着她道:“够了,你已经做得很好,真的。方才我看了都解气呢,更何况是敞亮开阔的君千纪呢。你若是安好,想来他也是能够安息的。”
凤时锦双眼通红,扭头就又想折回去,“不行,不行……还有我孩儿的性命,还有国师府那么多条鲜活的生命,我都不曾报复在他们身上!我得回去,再打一次……”
“阿锦,”苏徵勤将她抱起,不顾她的挣扎,大步离开了天牢,他道,“你也说了,他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答应你,那一天会让你亲眼看着。”
凤时锦在苏徵勤怀里安定了下来,头靠着他的肩膀,脸色白得可怕。
苏徵勤将她放回了马车里,许久她才慢慢地缓过神来,头晕晕沉沉的。苏徵勤手探了探她冰凉的额头,道:“许是有些中暑,我们回宫吧。”
马车摇摇晃晃地,摇回了凤时锦的理智。她声音又干燥又低哑,道:“我听苏顾言说,最后你在江山和我里面选择,你还是选择了江山。”
苏徵勤一愣,抬眼看她,见她抬手遮挡着双眼,避开窗帘外时不时流泻进来的强烈光线,只留下一道完美而削瘦的轮廓。
苏徵勤问她:“阿锦,我没选你,你很失望吗?”
凤时锦道:“没有,我知道你会选你的江山。没有任何东西在你心里强得过那样的**。所有你的爱,在那**的驱使下,都可以变成无所谓和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