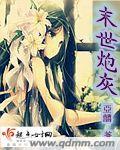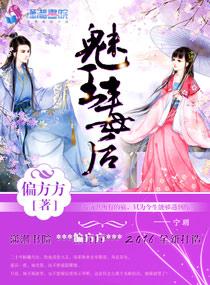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大郎该吃药了原文 > 第189章 功亏一篑(第2页)
第189章 功亏一篑(第2页)
他们的目光转向那满脸惊恐之色的耶律夷列,跨步上前,如拖死狗般拖着耶律夷列走出了营帐。
而耶律夷列此时也察觉到了不妙,连忙开口哭喊道:“武植,你不能这样,本王乃是辽国皇族,本王还有用啊,本王可以为你提供辽国的情报!”随着他的声音渐行渐远,随后便传来了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而随着耶律夷列所统领的剩余两万辽军被完全击溃,当下整个辽国西京道内,除了西京大同府还驻有部分兵力外,其余各城池州府无比空虚,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武植率领着大军接连攻克武州、应州、河阴、怀仁等城池州府,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兵临西京大同城下。
正当武植准备聚集大军,一举攻克大同城时,朝廷的一封加急令报却传到了武植手中。
武植神色凝重地望着手中的急报,眉头紧锁,沉默良久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地对着身旁的亲卫说道:“迅速传令,召集军中所有将校前来议事。”营帐内的气氛也随着他的神情变得压抑起来。
片刻之后,王进、林冲、呼延灼等一众将校纷纷齐聚于营帐之内。
“大帅,是否要对大同府发起进攻了?”呼延灼脸色兴奋地问道,其余将校也都纷纷将目光投向武植。
武植微微摇头,眸中滑过一抹无奈之色,沉声道:“本帅方才接到朝廷急讯,官家有旨,令本帅即刻自辽国班师回朝。”
“什么?”武植话音刚落,王进、林冲、呼延灼、毕仲游等一众将校几乎同时起身,齐刷刷抬眼望向武植,脸上皆写满了震惊与疑惑。
“大帅,目下我军已然兵临辽国西京大同府城下,此城一破,自开国之际失陷的燕云十六州疆土便能半数光复。大帅,此时撤兵,岂不前功尽弃?还望大帅三思!”众将校纷纷开口。
武植眉头轻蹙,目光徐徐扫过众将,沉声道:“此乃官家亲发的加急诏令,你我皆为大宋臣子,难道诸位想要陷本帅于抗旨不遵之罪?”
武植言罢,长叹了一口气,继而神色恢复坚毅:“官家既已下令我等撤军,那我等遵照执行便是。想必朝中定有要事发生,否则官家不会这般急切。”
说罢,他便传令下去:“迅速收整营地,准备撤军事宜。”
诸将校听闻武植此言,虽心有不甘,但也无奈地领命,走出了营帐外。
三天的时间内,武植领着2万大军撤到了朔州城。
驻扎在朔州城内的韩世忠,望见武植率军归来,心下满是疑惑,赶忙上前问询。
待听闻是朝廷下旨命武植从辽国撤兵,不禁惊愕出声:“什么?这是为何?如今我军在辽境势头正盛,为何要在此时撤兵?”
“想必是朝中有大事发生,不过我等身为臣子,既然官家如此命令,我等执行便是。”言毕,武植也传令韩世忠着手准备从朔州城撤退之事。
韩世忠听闻此令,望向眼前这好不容易才夺下的城池,心中闪过一丝不舍,此刻却要再度弃之,怎叫人不心生遗憾,可圣命难违,他也只能暗叹一声,领命而去。
武植率大军从辽国撤回,抵达代州城时,又见一队朝廷的传旨宦官在城中候着,而旁边的童贯脸色阴沉难看。
传旨官远远望见武植率军归来,一直紧绷的神色终于舒缓,长舒一口气后,疾步上前,神色庄重地说道:“武大人,此乃官家发来的加急圣旨,还望大人稍整军容,即刻接旨。”
武植与麾下众将校齐齐抱拳,躬身而立。
传旨官上前一步,缓缓展开那明黄的圣旨,双手捧于胸前,高声宣读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辽邦已与大宋重新开启和议之程,着武植即刻收兵,停止对辽国之征伐,速率军撤出辽境,不得有误。钦此!。”
传旨官宣读完圣旨后,将其递给武植。武植接过圣旨,眉头紧锁,声音低沉地问道:“这位公公,朝中到底发生了何事?为何偏偏在此时让本帅撤军?”
“武大人,辽国派来的议和使节已然抵达汴京。在蔡京蔡大人的极力斡旋下,我大宋与辽国已初步达成和议之态。朝廷此番急令大人撤军,正是担忧继续交战会破坏这刚刚促成的议和形势。”
传旨宦官因往日与武植有过往来,知晓其为人,故而对武植的询问未加隐瞒,如实相告。
旁边的童贯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冷哼一声,开口道:“我看这蔡京定是收受了辽国使节的好处!武大帅的军队已然快要攻破辽国西京大同府,如此大好局势,怎能轻易言和?”
童贯作为监军,本想着若武植大军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也能跟着沾光,在青史上留名。岂料这大好局面竟被蔡京给搅和了。虽说他过去和蔡京关系不错,但此刻也不禁怒火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