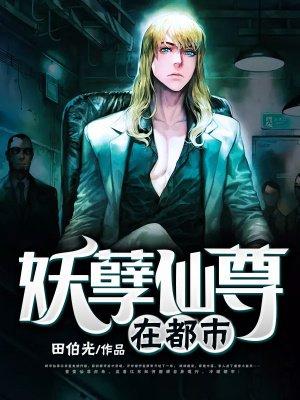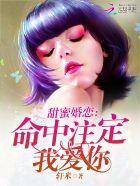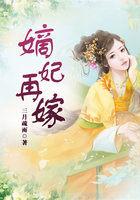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24章(第1页)
第24章(第1页)
刘炫曾就这个问题问难于何休:所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新王上承天命,必定要改正朔,若依此说,鲁国纪年被称为“元年”,这就意味着天命抛弃了周王室而降临鲁国,也就意味着鲁国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鲁国自当改正朔才对,为什么仍然奉行周历?这不是自相矛盾么?203
刘炫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而当初《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要写“王正月”(周历正月),说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统”。
(二)公羊三统论
1.大一统:并非“大统一”
“大一统”是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但其古今词义早已发生变化了。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容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似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接下来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天命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令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204
“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为天地之始;春,为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为人事之始。205《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206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有“春秋五始”的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据何休“统者,始也”的说法直接把“大一统”解释为“大一始”,进而言之:夏、商、周三代历法,一年的开始各自不同,这时有杞国保存了夏历(杞国是夏的后裔),有宋国保存了殷历(宋国是殷商的后裔),除此之外,天下都以周历的一年之始为大。一年之始由此而得到确立,是谓“正始”,使天下都知道周天子是最高领袖。207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义的第七项是:“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就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从这三个例句来看,后两个确乎都是“总括,综合”的意思,而对何休的说法,却只照顾到“总系之辞”而忽略了“统者,始也”,显然只把“大一统”的“统”字理解为“总括,综合”是不确切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说文解字》:“统,纪也。”释“纪”字为“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208
《淮南子·泰族》有一处“统”、“纪”连称,颇能说明问题:“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209这是在说人性需要加以引导的道理,用缫丝来作比喻,说蚕茧是可以从中抽丝的,但如果不经过女工用开水煮熬,抽出蚕茧的“统纪”,那是怎么也抽不出丝线的。——这个“统纪”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是指丝线的线头,所以“统”字是可以引申出“开端”之义的。即便如惠栋不满意把“统”字解释为“纪”,但他自己所作的释义也与此相近——惠栋引《易经》“乃统天”句下郑注:统,本也;又引《公羊传》:“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210
周代是宗法社会,周人自有敬奉始祖的政治和社会风俗,那么,作为“重视开始”之意义的“大一统”显然倒也符合于春秋的时代背景。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便又该回到“王正月”之“王”到底是周文王还是所谓“时王”的问题上了。
孔广森由此作了一个估计,说大约周代初年颁布历法是在周文王的祖庙里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是第一任受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211
孔的这一推论看似合情合理,他站在公羊立场上捍卫信仰,而当代治《左传》的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造字:左“君”右“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造字:左“君”右“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着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来,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之“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自用是楚历,并非周历。杨并且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却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自用夏历,不用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之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