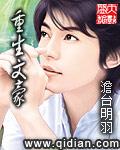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25章(第1页)
第25章(第1页)
杨说考据精当,最后这个结论却有些草率了,他这是把《公羊传》中作为“重视推尊开始”的“大一统”混同为秦汉以后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了。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统一”了?
汉代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讲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213联系上下文来看,路温舒把“大一统”基本理解作“慎始”,随后又是“正即位”,又是“初登至尊”,又是“正始受之统”云云,很有几分公羊学“五始”的味道。大体可以判定,虽然路温舒并不以学术知名,但他“受《春秋》,通大义”,214对“大一统”的理解大略就是《公羊传》的本意。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源头大约在董仲舒身上。董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15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无所适从。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断绝。只有让邪说灭绝,才能“统纪可一”、法度明确、民知所从。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而“统一”的观念则广为人们接受——毕竟这看上去是符合常识的,正如杨雄《法言》所作的一个类比:“一个小市场不胜争论,一卷书不胜异说,所以市场上需要由官方制定统一的物价标准,一卷书也必须设立经师。”216多元化的好处与必要性是非常晚近才广为人们认识到的,正如繁花丛生的多是沃土,满目黄茅白苇的则是贫瘠之地。217而被混淆为“大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则在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由手段升格为目的。汤因比曾经这样描述统一国家的特征:“当统一国家一旦建立之后,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求生的顽强性,但是绝不能把这种顽强性误认为是真正的生命力。这倒毋宁说它是不肯死去的老年人所表现的那种顽固的长寿欲望”,并且,统一国家还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像它本身就是目的的行为倾向”。218
2.夏之忠,殷之质,周之文:天人合一的历史循环论
在公羊学中,还有一个和“一统”很有关联的要紧概念,叫做“三统”,和前述的“三正”(夏正、殷正、周正)近似。——《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朱熹《四书集注》,这里所谓的“世”,指的是朝代,219“十世”也就是十个朝代。子张想问的不是历史,而是将来,也就是说,将来难免会有很多改朝换代的事情,世界也会屡屡出现变局,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推想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孔子的回答是从历史着眼的,正所谓鉴往知来:“殷代因袭了夏代的礼仪制度,加了些,减了些,都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加加减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以后,礼仪制度无非是在这些原有内容上继续加加减减而已,当然是可以推知的。别说十世,就算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作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原则虽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的,但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大原则都不会变。孔圣人之所以能够洞悉未来,是因为他能够深明个中规律,此即“古今之通义也”。220
这一思想,上承韩愈道统论,221下启道学风潮,如余英时谓:“……所谓“上古圣神”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而言(见《大学章句序》),他们都是德、位兼备,即以圣人而在天子之位者,因此才有资格“继天立极”,传授“道统”。在这个意义上,“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则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以“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孟子·梁惠王下》)之“统”是相通的。这是《中庸序》中“道统”二字的确诂,毫无可疑。”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