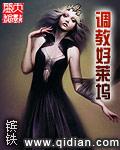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69章(第1页)
第69章(第1页)
当然,非要说这个情理的话,后世即便是唐玄宗那样的明君,也干出过类似的事情。若论周代的主流婚姻观念,李衡眉曾经论说过“翁媳不婚”这一禁忌——从《礼记·大传》入手,指出其中所谓“男女有别”的深层涵义是指翁媳不得婚和母子不得婚,这一禁忌当起源于辈行婚,即严格禁止相邻辈分的人之间的性关系。在周代,不但实质上的翁媳不能结婚,就连名义上的翁媳也不能结婚,比如《毛诗序》讲到,卫宣公犯了这个禁忌,有人就作了《新台》一诗来讽刺他。615
行辈之禁忌,依李说:“周代是严格禁止母子通婚的。《礼记?曲礼》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并把这一禁规从血缘关系上的母子推广到名义上的母子,即不问生母或庶母,只要具备母的名分,儿子就不能与之通婚。如果违犯,就是十恶不赦,并用‘烝’、‘报’等字眼来谴责这类不轨行为。”616
但是,上述《礼记》之说恐怕未必确实,大约是以汉人的道德观来描述周人,毕竟时空的间隔会拉大道德伦理的隔膜。正如清人刘献廷所谓:“后之儒者,以汉、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617这是古人读史的卓识。的确,若仅依《左传》,烝和报并不含有贬义,甚至是男人应尽的义务,618这应是一种古老婚姻习俗的延续。619
如果确实存在“翁媳不婚”这一婚姻禁忌的话,可想而知的推论就是:违禁婚姻所生下的儿子也很可能会受到大家的歧视。那么,联系到鲁惠公一家人,就算鲁惠公活着的时候可以关照仲子所生的儿子(即鲁桓公),但在他死后,鲁国的公论恐怕很难认同鲁桓公吧?——这又可以向两个方向作出推论:要么《史记·鲁世家》里公公娶儿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么鲁桓公继位的合法性一定会受到公论的质疑。
但是,也许“翁媳不婚”的禁忌值得商榷,毕竟仅以《礼记》和《毛诗序》来论证春秋史实怎么说也还隔了一层。而反面意见虽然也没有提出什么坚实的证据,但也值得参考一下——童书业即认为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和春秋时代家长制家庭的婚姻状况是吻合的,大约贴近实情。620那么,如果童说属实,621这对司马贞和马骕他们来说还意味着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很难脱离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的心理陷阱,何况很多善恶之别都是随着时代风气而风吹幡动的,时人眼中的“禽兽不如”换到古代,或者换一个时间、地点,未必就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古人大多不能领会这层意思,而认为人伦便是天理。622
事情还有另外的说法,《榖梁传》就把仲子说成惠公之母(也就是隐公和桓公的祖母)而不是桓公的母亲。623有人认为大有可疑,比如朱熹;624也有人力挺此说,比如清人刘逢禄;甚至还有说仲子是隐公之母的,如明代季本;625顾炎武还推测鲁国有两个仲子,一是孝公之妾,一是惠公之妾。626众说纷纭,又是《春秋》之一大疑案。
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是今文学派向古文学派的一次总攻,仅就眼前这个仲子问题,刘认为《左传》的这段文字是刘歆为了使《左传》看上去更像一部释《春秋》之作而篡改过的(刘逢禄认为整个《左传》到处都是刘歆动过的手脚),司马迁写《鲁世家》的时候所采用的应该是原版《左传》,而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却依据篡改版《左传》来怀疑《史记》,实在不该。而且,《史记》里也并没有说那位宋武公之女叫做仲子。627
虽然时至今日,刘歆大规模作伪之说已经不大有人相信了,但经中疑点仍在,殊难贯通。清代于鬯《香草校书》也是从《左传》和《史记》之间的龃龉作出分析,说出了另外的一番道理:《春秋》记作“仲子归于我”,“我”字底下按说应该写明到底是“我国”的哪位国君才对,比如归于我隐公,或者归于我惠公。《春秋》却不写明,谁知道仲子究竟归于谁呢?及至读《史记·鲁世家》,才知道此事大有难于措辞之处。《鲁世家》的记载是:“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这里所谓嫡夫人,指的就是惠公的元妃孟子;所谓“贱妾声子生息”,指的就是继室声子生隐公;所谓“息长娶于宋,惠公夺而自妻”,就是《春秋》所谓的“仲子归于我”。照此说来,仲子本该归于隐公而实际上嫁给了惠公,所以《春秋》既不能说“归我隐公”,又不便直说“归我惠公”,只好闪烁其辞地记作“归于我”。这段一定是鲁史旧文,当初史官落笔的时候一定是大费斟酌的。
至于仲子手上的“为鲁夫人”,假如仲子嫁给隐公,可那时候惠公尚在,隐公又不是太子,仲子是没机会作鲁夫人的。所以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惠公夺了儿子的未婚妻,无以自解,便找理由说是为了达成仲子手文上的预言。
如果没有《史记》的这段记载,《左传》之文便读不通顺。《左传》是明知其事之原委但故意藏着不说,还添上了一段手文预言的玄虚故事。多亏《史记》详记其事,与《左传》两相参合,当无可疑。而且,不止《左传》有疑点,《公》、《榖》两传于此也有迹可寻。《榖梁传》说:“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公羊传》说:“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如果仲子真是夫人,声子真是媵妾,那么桓公是夫人之子,隐公是媵妾之子,隐公让国给桓公又怎能说是“非正也,邪也”,更怎能说是“成父之恶”?尊卑如此显而易见,又何至于“国人莫知”?——原因在于:隐公虽然是媵妾之子,媵妾的身份却正;桓公虽然是夫人之子,夫人的身份却不正,所以《公》、《榖》二传才会这么说。由此可见,“三传”的作者全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是都不明说而已。从《史记》推断,“三传”的疑点便豁然贯通了。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