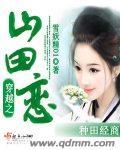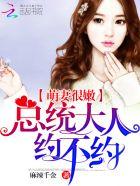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90章(第1页)
第90章(第1页)
及至清代,黄中松作《诗疑辨证》,辨析周人先贤古公亶父的名字,说不能一看见“父”就认为是字,从《左传》来看,以“父”为字的虽然很多,但以之为名的也不是没有。黄虽然在“以‘父’为字”的例子里列举了邾仪父,但他“不能一看见‘父’就认为是字”这个结论显然更加重要。814
顾炎武也感觉此事可疑:附庸小国无爵可称,如果直书其名,显得不够客气,不是待邻国国君之道,那就称字好了,以示其地位低于子爵、男爵而高于夷狄。所以,《左传》说“贵之”,《公羊传》说“褒之”,都没道理。这无非是鲁国史官记事的常例罢了,并不是鲁史本来写作邾克,而孔子特意改成邾仪父以示微言大义。815
持此论者还有人在。顾栋高引方苞的研究,说“仪父”根本就不是“字”,而是“名”——不要以为凡是带“子”、带“父”的就都是字,这太过笼统了,比如介子推、仪行父等等,都是名而不是字。《左传》说邾仪父名克,其实从时间上推算,邾仪父和邾克是两个人,邾克是邾仪父的儿子。
方苞的分析不止为顾栋高一人采信,而问题是,经学家如果信了方苞,原本的微言大义就需要修订。清儒郝懿行《春秋说略》就是这样,认为“仪父”是名而非字,《春秋》之所以称邾仪父,是因为邾国当时只是附庸小国,地位低,等后来有了爵位了,《春秋》才以爵位称之。郝认为这才符合春秋大义,因为经文称“公及邾仪父盟于眜”,按照《春秋》的书写体例,这个“及”字是有讲究的,只能由内及外,不能由外及内——这个内,指的是鲁国;外,指的是外国。(案:就像现代的中日邦交会谈,双方写字留念,中国这边的只会写“中日友好”而不会写“日中友好”,日方同理。)这就是“以内及外”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是“以大及小”,鲁国是侯爵国,邾国是附庸国,所以要先写鲁国,然后才“及”邾国,如果写反了,那叫“以贱及贵”,就不对了。816
这样看来,“仪父”到底是名还是字,实在关系重大,影响到国际关系上的一些原则问题。如果真让方苞他们说对了,旧的微言大义便有根基被动摇的危险,而新的微言大义则会趁虚而入。这问题是非名即字,非黑即白。方苞的说法斩钉截铁,总而言之就是:“《春秋》从无书字之法。”顾栋高以方说为据,详驳胡安国,从《春秋》经文连连举例,让胡安国理论难以自圆其说。顾最后说到杜预对《春秋》里凡是称名的都认为是孔子的贬斥,但《春秋》的编写体例若当真如此,子贡那些孔子的高足们肯定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但孔门后学在鲁哀公十六年续写《春秋》(见于《左传》),记载老师之死,其用语却是“孔丘卒”,而非“仲尼卒”,难道连孔圣人也一道贬了不成?817
再说宋代《春秋》学,也并非孙复、孙觉等人一统天下,以文学知名的“三苏”对《春秋》都有研究。苏辙的《苏氏春秋集解》就是一部著名的走朴实学风的专著。对孙觉等人的义理,苏辙找出了有力的反例:你们不是说孔子在《春秋》里凡是会盟都是贬斥吗?可孔子在《论语》里明明盛赞过齐桓公九合诸侯,还说要不是管仲出力,我们早变成野蛮人了。《孟子》谈到孔子著《春秋》,也引孔子的话大谈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看来,孔子怎么可能反对诸侯会盟呢?818
苏辙的反驳是相当有力的:如果《春秋》的孔子和《论语》的孔子不存在矛盾,那么把《春秋》对会盟的记载视为孔子的贬斥就没道理。苏辙是否也像何休那样,认为对邾仪父的称字体现了孔子的褒奖呢?苏辙认为,《春秋》对会盟时间的记载仅仅出于客观理由罢了,而许多经学家都相信其中也是蕴藏褒贬的。——具体到邾仪父这个例子里,就是会盟的时间:“三月”。
苏辙是朴素的,孙觉他们是“深刻”的,由此可以管窥当时蜀学与洛学的一点异同,也可以看出时代背景与政治风貌对学者干扰程度的深浅。及至元祐年间,“蜀洛交争党祸深”,819学术之争伴随政党之争(所谓党争,至少从攻讦者的表面言辞来看),掌握真理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了。《汉书·终军传》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那是在诸侯会盟问题上两方各执春秋大义互相辩难:
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奉命巡视郡国风俗,擅自准许膠东国和鲁国冶铁晒盐。等徐偃回京交差,很快便大难临头:大法官张汤认为徐偃的矫制行为是国家大害,徐偃论罪当死。——张汤的说法确实在理,但问题是,其一:汉武帝时代正是个新旧鼎革的临界点,其二,徐偃到底也是位博士官,经学水平远比张汤要高,而当时的经学几乎就是实用政治学,所以,徐偃在这生死关头引春秋大义辩驳道:根据《春秋》精神,大夫出疆,如果遇到有利于社稷、百姓的事情,是可以不经请示而专断于外的。
徐偃搬出了春秋大义,张汤可没话说了。此情此景,汉武帝派出了终军协助审案。终军对徐偃,以春秋大义对春秋大义。终军说:“古时候的诸侯国,百里之隔即风俗有别、不能相通,互相之间常有会盟之事,安危形势常在呼吸之间,所以你为自己辩护的那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可现在世界变了,天下一统,万里之内同风同俗,正是《春秋》所谓‘王者无外’,天下四方全是皇帝的地盘。你说什么‘大夫出疆’,现在哪有出疆可言?”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