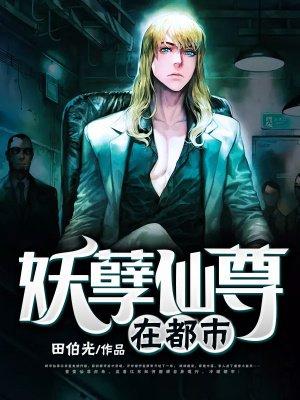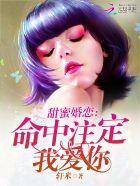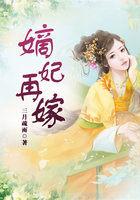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隐公元年注疏 > 第91章(第1页)
第91章(第1页)
终军驳徐偃的话还有不少,不作详引,后来徐偃理屈词穷,只好等死,而终军的这番诘难大受汉武帝欣赏,还被下发张汤学习。但是,切莫以为“王者无外”就真的战胜了“专断于外”,同是汉武帝时代的吕步舒审断淮南王谋反案,本着“专断于外”的春秋大义整掉了好几千人,同样大受汉武帝的表彰。
无论如何,《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所记毕竟是封建社会的陈年旧事,越来越难适应于皇权专制的社会转型了。一般来说,不论是圣人经典还是民间曲种,凡遇到此种情况,前景不外二途:要么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要么就与时俱进,主动去适应一个又一个的新时代、新风貌。前文中孙觉等人的解经就是一个典型:要在皇权社会里阐释封建思想(这里用“封建社会”的原始意义),阐释得越深刻,或许就离经典的本义越远。就这类思想典籍来说,政治与学术毕竟是在两条路上,政治上要与时俱进,学术上要溯本求源,渐行渐远也许才是正常之态。
关于邾仪父和鲁隐公的这次的盟会,历代专家们在义理上作了无穷的辨析,但从事实来看,称名和称字的原因也许相当单纯,这点可以参照徐复观对周代姓氏问题的一段分析:“西周以前,姓氏两个名词,常常可以互用。自周初始,则姓以标国,氏以标族。有氏始有族,否则在小宗五世之后,只能算是无所系属的孤单的一人一家,此时虽可向上追溯于他的姓,但姓只能由大宗、国君代表,他人不能称用,等于没有姓。所以“《春秋》隐、桓之间,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既未赐氏,又不敢称姓,故仅称名。如在国外,既不能称姓而又无氏,则在名上冠以国名。如宋之公子朝,在国外则称宋朝;卫之公孙鞅,在秦则称卫鞅者是。”821
(六)地期与时间,小信与大信
问:“公及邾仪父盟于眜”,这个“眜”是指什么?
答:这是指会盟的地点。(“地期也”)
——这里又遇到《春秋》所谓“义例”。邾仪父和鲁隐公相约于蔑(眜),举行会盟仪式。何休说:“‘公及邾仪父盟于眜’,这个‘于’字也是大有深意的:‘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以地定事者不加于’。”徐彦跟着解释,822大意是说:比如张三在北京,李四在海南,某天通了个电话,约好第二天飞到上海签个合同,按照《春秋》笔法,这件事就可以写作:“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可如果北京的张三和海南的李四同在上海办事,某天两人通了个电话,然后见面签了个合同,按照《春秋》笔法,这件事就不能再说“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了,而要说成:“张三来上海办事,遂及李四签了合同。”——这个分析主要是从文法上着眼。公羊学家不光讲大义,也讲文法的。
当然,文法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大义:从“于”字上嚼出了文法,从“三月”这个看似单纯的时间记录上嚼出了大义。何休认为,虽然孔子对邾仪父的这一作为作了表彰,但总体而言,凡书盟者都是批评。大家搞盟誓总要指天划地的,说些诸如“谁反悔谁就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大非君子之风。从《春秋》书写体例上看,凡是把盟会时间精确到“日”(书日)的,都是暗含批评,意思是以盟日的历历在目来彰显会盟者的背信弃义,而会盟者之间的诚信是为“小信”。
有“小信”当然也有“大信”。“大信”在时间记录上不是精确到“日”,而是精确到“时”(季节),比如,同样是“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但“2000年春,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和“2000年1月15日,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所表达的褒贬完全不同:前者表示“大信”,是褒,暗示着张三和李四都是信约守诺的模范市民;后者表示“小信”,是贬,暗示着张三和李四后来撕毁合同、背信弃义。
但这一分析联系到邾仪父身上,却有些让人糊涂了,因为《春秋》对邾仪父和鲁隐公的这次会盟既不是书日,也不是书时,而是取了个中间值——书月,即“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眜)”,这个“三月”又该怎么解释呢?到底是褒还是贬呢?
另一个问题是:前边才讲邾仪父称字表示了孔子对他的褒奖了,应该不会又用书月来表示贬斥吧?
何休和徐彦的意见是:称“邾仪父”表示褒奖,称会盟日期表示贬斥,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之褒,是因为邾仪父第一个慕新王之义前来修好;后者之贬,一是因为会盟之事一般都该贬一下的,二是因为从《春秋》后文来看,在鲁隐公七年有“公伐邾娄”,两国又开战了,可见隐公元年的会盟是小信而非大信。823
事情当真如此吗?毕竟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总免不了有一些来往,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约定,为什么孔子(或公羊家眼里的孔子)对会盟之事采取如此的态度呢?那么,既然会盟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是免不了的,他(他们)又认为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
公羊家对此是有过正解的。何休和徐彦搬出《春秋经·桓公三年》的一段话作为榜样:“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824这是说:桓公三年夏天,齐侯和卫侯在蒲这个地方“胥命”。——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里表示时间的词是“夏”,也就是依“书时”的义例,既没有记载月份,更没有记载具体日期。而所谓“胥命”,依公羊家的解释,也是一种会盟,和一般会盟的区别是:一般会盟要搞歃血仪式,胥命却没有这种仪式。《公羊传》是赞许“胥命”这种方式的,并总结说:“古者不盟,结言而退。”825这就是说,古人社会风气好,如果要有什么约定,口头一说就够了,不搞发誓赌咒立盟约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