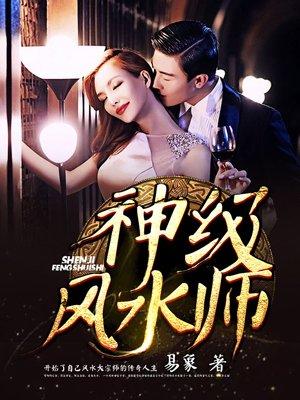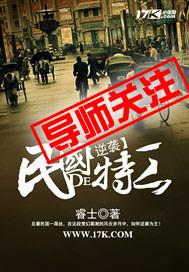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历代大儒传 > 第77章(第1页)
第77章(第1页)
质&rdo;。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
他说:&ldo;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rdo;就像立身屋檐底
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
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ldo;师师相传&rdo;,代代相袭,殊不
知&ldo;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rdo;(《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
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ldo;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rdo;
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
&ldo;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
见弥大。&rdo;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ldo;多奇观也&rdo;。而&ldo;百
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rdo;他又说:&ldo;大川相间(兼),
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rdo;倘若&ldo;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rdo;?
人做学问也是如此,&ldo;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rdo;(《别通篇》)其渊
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
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
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ldo;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rdo;并且认为:&ldo;儒
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rdo;(《超奇》)儒生托身儒门,
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
世务,不通古今,&ldo;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rdo;(《效力》),故不及博览
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ldo;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rdo;(《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
要&ldo;好学勤力,博闻强识&rdo;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ldo;通人览见广博,
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rdo;,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ldo;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