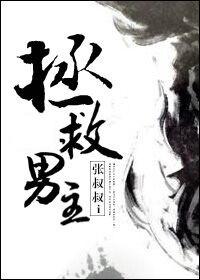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狂倾天下之半缘君 > 第一百二十四章 口是心非(第1页)
第一百二十四章 口是心非(第1页)
“想过。”于文筠点头,“能做到不露一丝痕迹就把琰儿带出宫,且能避过所有禁卫,除非是熟知宫中情形且有一定权势的人,否则不可能不被人察觉……只是那人做得太过滴水不漏,这些年来我一直查不出到底是何人所为。”
楚清欢一时没有开口,能把事情做得如此周密,定然不是简单人物,而普通宫人即便有偷偷出宫的可能,也断然没这个胆量,更没这个动机。
想到此,她便向于文筠细细地询问了莒卫朝中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与王室宗亲的情况,但听下来亦没有明显的可疑之处。
她沉默半晌,遂道:“你与于琰的生母并非皇后,而是已故的淑妃,那皇后……”
“不会。”于文筠知道她要说什么,肯定地道,“在琰儿出生之前,皇后便已一心向佛,虽未入佛堂,但已极少过问后宫之事,皆交由我母妃代为主事。我母妃因生琰儿难产西去后,皇后才重新开始打理后宫,平日里吃斋念佛,甚是安定,对诸妃嫔也颇为宽待。”
既是这般说了,楚清欢便也不再多说什么,道:“不管如何,于琰无故被掳出宫外,之后又险些殒命,此事必是有人暗中筹划。是蛇总会露出尾巴,任何事也不会有头无尾没有目的,只是缺少现形的机会……不如,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
她眸光陡地扬起,冷锐之色隐现,“文筠,你说呢?”
------
楚清欢前脚跨进门槛,正要关门,后面一只脚就伸了进来,将门一挡,随即大步跨了进来,反手将门关上。
她回头,轻轻挑眉:“还不去睡……”
下一刻眼前景物一转,身子已被紧紧压在门上,夏侯渊欺身而下,俯了眉眼盯着她:“明日随我回兆京。”
命令式的语气,再加上肃然的神情,可见是认真的。
楚清欢看了他一眼,抬手摸摸他额头,“没发烧?”
他一把捉住她的手,沉声道:“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却当你在玩笑。”她道,“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不可能回去。”
“那是别人的事,与你无关。”
“怎么是别人的事?”她皱了眉,“你是知道我性子的,于琰既然认了我作姐姐,我就不会置他与于文筠不管。”
“那是人家的家事。”他重了语气,很是不悦,“你这也管,那也管,什么时候能管管我?”
屋内没有点灯,看不清他此刻的脸色,但那层抱怨却是清清楚楚,毫不掩饰,就象一个要不到糖的孩子跟大人抱怨一般。
她不为所动,语气未改:“我什么时候不管你了?”
“那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我们成婚。”他极是霸道,“只要你跟我成婚,别的事随便你怎么管,我再不阻拦。”
只要跟他成婚,便什么事都不再阻拦?
她可不可以认为这是威胁?
“你先回去睡一觉。”楚清欢推了推他,“睡醒了,你就想起我曾经跟你说过什么了。”
“我清醒得很,不想睡觉。”夏侯渊猛然箍紧她的腰,低头狠狠地咬住了她的唇,含糊地说道,“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先把你给办了。”
他咬得有些重,她不免吃痛,由得他唇舌直冲而入,肆意作为。
自从那日在巩州城外的河边应了他之后,他便有机会就要逮着她亲热一回,虽然每到最后总是激情难抑,几欲冲破防线,但他却也定力强悍,生生克制住,说是要等到大婚那日才要她,不想这般委屈了她。
她倒是没觉得所谓,一旦决定了接受他,就不会再瞻前顾后,扭扭捏捏,他既忍得住,也随便他。
只是现在,他倒是忍不住了?
“不想留着到大婚了?”她的声音里忍不住带了丝取笑的意味。
“不想了。”他的唇自她颊边滑过,卷起耳珠,一只手掌自她衣襟处滑了进去,“今日是良辰吉日,适合洞房。”
一声轻笑从她唇边逸出。
他微恼,手下重重一捏,“你太不让人省心,现在不办了你,谁知道你又要跑哪里去。”
“不是我不省心……”她轻轻一喘,抬手抽去他的束冠玉簪,顺滑如水的墨发便泻了她一手,“是你自己心里没有安全感……枉你是个男人,还是一国之君,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他应得顺畅,“你说得对,确实自信不够……只有让你成为我的女人,你才会乖乖地留在我身边……”
她微微一怔,本以为以他那高傲的心性,这话定是要否认的,没想到竟如此坦白地承认了。
未及思考,腰带不知何时已被他解开,里外衣物皆是大敞,他的手掌游移于肌肤之间,所经之处,掌心的薄茧带起丝丝的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