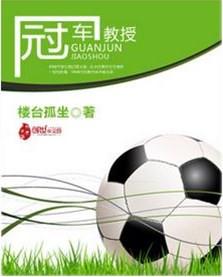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本侯有疾晋江 > 第312章(第1页)
第312章(第1页)
杀不得还打不得吗?
他们原本只是起了捉弄的心思,趁着燕宁越注意不到将人捉弄一番,或是故意打翻对方的砚台却装作是不小心的,又或是将人的书藏了起来,再使劲地踩踩刘维汉的脚。只是没想到刘维汉竟然这么懦弱,连半点反抗都没有,甚至不曾和燕宁越说,于是他们也就越发的胆子大了,将人打了一顿,又威胁刘维汉不得说出去,不然要他好看,一个匈奴人在大晋,就该缩着脖子做人!
燕宁越抿着唇想了半天,想不出如何惩罚人,便去看刘维汉,但刘维汉的性子说得好听是温吞,难听些就是胆小,他哪里敢想如何惩罚人,便又盯着自己脚下看。燕宁越无可奈何,只得对着祭酒道:“请祭酒为维汉做主。”
祭酒气得脸色铁青,前一日还答应得好好的,说是要压下此事,今日就将这件事翻出来,闹得整个国子学里人尽皆知,等明日,整个长安的人都知道他这个祭酒管不住学子,叫人家挨了打还不敢声张,他的脸面在哪里?他的仕途又在哪里?
若不是长公主……!
“此事需要慢慢定夺。”祭酒冷冷地道。
一个孩子能泛起什么大风浪来,难不成长公主还会因为一个孩子去了他的职位不成?一个孩子的委屈重要还是匈奴的事情重要?孰轻孰重孩子不懂,想来孩子的兄长一定省得。
燕宁越再是年幼也听得出祭酒话里的推诿来,也生了几分失望之心,这就是国子学的祭酒,被他们敬重的师长,竟然是这副模样。连长公主都觉得不对的事情,对方竟然不肯悔改。
“敢问祭酒,您需要定夺多久?”他不卑不吭地道。
“这事也是你能得知的吗?”
“我等如果不能知,那谁能知?”
“燕宁越,你在质问我?”祭酒沉着脸看着他,“你在质问你的师长?兵部尚书便是这样教子的?燕侯便是这样教导你的?”
燕宁越真的很不喜欢别人提起他的父兄,尽管这是每一个勋贵子弟都会经历的事,外人会对他的父兄的事迹津津乐道,像是一笔谈资,若是拿得出手便吹捧,拿不出手便嘲讽。燕宁越以自己的父亲为傲,以自己的三个兄长为傲,每次被说是兵部尚书之子、燕侯之弟他都很开心,但并不代表,这种形式的提起他也开心得起来。很多时候,别人对他提起燕侯,要么阿谀奉承,要么明夸暗讽。
“祭酒,我昨日拜见长公主。长公主对我说,匈奴之事于我等无关。孔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等是学生,我等受了侮辱,我等为何不能问?”
“既然是学生,那便省得学生只需好好读书,谁叫你来质问长辈?”
“本宫已经听了半天了,不想再听了。祭酒年纪大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回家颐养天年罢。”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的长公主轻轻叹了口气,道:“你们怕是都忘了,国子学不止有祭酒,还有山长。”
祭酒的脸色一瞬间变得十分苍白。
……
刘维汉将脸上的伤养得完全好了,才在休沐时收拾了包裹回家。
汉中侯府在建宁坊,是长公主赐下来的宅子,一是显示天家十分重视汉中侯府,二是看管汉中侯府的人,防止出了什么意外。
“爹爹!”
刘行周到了长安已经一年有余了,因为闲来无事,便向长公主讨了一个整理石渠阁的差事。不过她一不看各地朝政记录,二不看历代史书,只看各个郡国的风土和一些家族记事,譬如某县有大族几家,姓氏为何,在某年从何处因何而来。
刘煜跟着她一起在做这件事,开始只是想找一找大晋姓陈的人家,看看能否和刘行周的身世对上,后来看着看着就入迷了。便是大晋从高祖皇帝至今的历史,各县的县志更迭,也要远远比匈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日子有趣多了。
“平安回来了。”
“哎。”刘维汉笑着应了一声,没看到刘煜的身影,问道:“阿娘呢?”
“前些日子从宫里拿出来的册子破损处已经补完了,你娘送进宫里去了,大约再有半个时辰就回来了。”刘行周看着他道:“今儿怎么这么高兴?”
刘维汉裂开嘴笑,道:“爹爹,我有个姓燕的同窗,他大哥是长公主的驸马。前些时候他去拜见长公主,长公主说匈奴不干我的事。”
刘行周眉头拧了起来,问道:“长公主怎么会突然问这个?你是不是在国子学里遇到了什么事?”
“他们说我是匈奴人,但我觉得我是晋人,我很喜欢大晋,我也很喜欢长安。匈奴不干我们的事。”
刘行周凝神看着他,良久,才露出了笑容,道:“长公主说得对,你说的也对。匈奴不干我们的事。”
刘维汉笑得更灿烂了。
“爹你和娘是不是在找什么啊?”
“你娘说我原先姓陈,是被你外祖父捡回去的。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点有联系的东西,若是找到你祖父,也多一个人来疼你。”
“爹爹姓陈,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姓陈?。”
“你姓陈了你娘怕是要将我从床上踹下去了。”
“爹爹……你再说真的要睡外院了。我帮爹爹一起找。”
“行,儿子没白养……”
作者有话要说: 倒也不必觉得站反了,我一贯是写互攻的,应当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