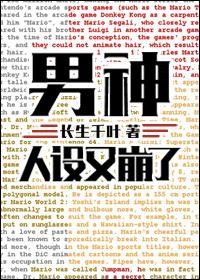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倾国倾情 > 第三百二十一章 笑面奴(第2页)
第三百二十一章 笑面奴(第2页)
她那时候不知道南五所是什么地方。
现在也仍然不清楚,可她的所有的骄傲……已经被搓磨的不剩半毫分了。
一转眼,距离上次萍芷过来,又不知道是过了多久,她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平日只能看到从窗户处能看到一方天地。
时而阳光灿烂,可见满园葱葱郁郁的夏日景色;时而大雨倾盆,将那绿色淋得如同要滴到地上去;时而有燕雀儿掠过窗口,留下滴沥沥的鸣叫声。
外面的草木并不开花,似乎也没有人修剪,便任意的疯狂生长着,枝条长成了张牙舞爪的样子。
若是白天,商雪袖便怔怔的看着那枝条,仿佛如此,因为看得到树枝的变化——每一片叶子掉落,或末梢每一对儿嫩芽萌出,她才有着些许生意。
到了晚上,那曾经在白天给她生意的枝条,便张牙舞爪起来,随着或明亮、或半隐半藏的月色,在窗子上投下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
微风起时,慢慢晃动,大风来时,舞动的便愈发的狂乱,仿佛能听到叶子在凌厉夜风中的嘶叫——这景象似曾相识,商雪袖却回忆不起来了。
但,这些并不是最让她害怕的。
她最害怕的夜晚,不管如何抗拒,如何不愿意,都一步步的到来了,每天都从不缺席。
外面脚步声响起,听起来是两个人,一人脚步轻,一人落脚重。
商雪袖瑟缩的躲在床角,瞪大了眼睛,看着一拢晕黄渐渐的从窗外一闪闪的到了门口,从门缝里透出光亮来,然后是开锁的声音。
她不由自主的抖了起来,最后竟然不可抑制,牙齿也咯咯的响了起来。
开门的一男一女进来的时候还因为长期为奴为婢,保留着无法改变的哈着腰的习惯,甚至脸上都是带着笑意,乍一看去,煞是和煦。
可商雪袖再清楚不过这两张看似和蔼、绝不会伤人的脸孔下隐藏着什么样的面目……
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一个夜晚便这样开始了。
一直到天到了蒙蒙亮的时候,商雪袖已经近乎呆滞了。
她有些听不清那个容嬷嬷在问什么,也听不清那个淮公公在笑什么,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
这些天,没有一天晚上不是如此,他们也许是怕有一天皇上会突然想起自己吧,所以不曾碰过她一个手指头。
他们只是坐在她的床前,“奉旨问话”。
在到了这里的前几天晚上,商雪袖哭闹过,甚至试图反抗过。
可那个嬷嬷力气那么大,使劲的绞拧着她的手腕子,脸上还是带着笑容,温言温语中透出了十分的阴冷:“娘娘还是别较劲儿的好,皇上说过,不让奴婢们碰您,但您要非这样,奴婢手下没个轻重,就不怕伤了筋骨?”
淮公公则尖声的笑了起来,道:“寻常人伤了筋骨,自然好了也就好了,但听闻娘娘原是名伶来着,这……有没有影响,可真不好说。不过娘娘既已进了宫,原本就不会再去做那些下贱营生,兴许不介意?”
商雪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可她一时间却真的怕了。
若真的筋骨受伤,表面看,养一养治一治都是能痊愈的,但对伶人的影响,却是极可怕的。
变成了“皇上”的阿虞,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