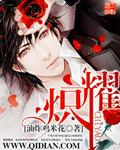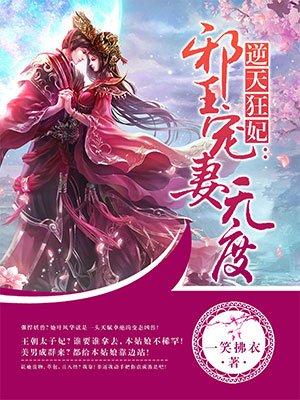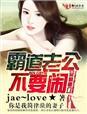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偷鸡技巧的意思 > 第153页(第1页)
第153页(第1页)
居意游认为首先要去魂牵梦萦了好久、却只能趴窗边欣赏的松花江看看,齐显认为不行,江边风大、全是冰看着就冷,很容易再次感冒。“你居然这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我只是觉得…”“干得好!”居意游拍拍他,“再接再厉,我就喜欢你的坦诚。”“…我只是觉得中央大街也不错,离得近。”“那快吃晚饭的时候去呗,吃完在街上转转,好久没逛过了。”许久没在中央大街看到这么多人了,他俩吃俄餐排俩小时、现在在马迭尔冰棍小摊前的人堆里挤着。按理说齐显会难受死,可是他开始有点觉得这是好事。鲜活,是疫情期间绝对没有的鲜活。“唔。”冰棍很没礼貌地杵到嘴边。“想什么呢?来一口。”居意游手里冒着寒气的冰棍在他嘴巴上试探。“我不——咳咳!”这股寒气飘进嘴里,冰得喉咙一阵收缩。齐显不理解,是东北不够冷吗?为什么冬天吃冰棍?他不是个合格的东北人,他不仅不吃冰棍,怀里还抱着超大杯热气腾腾姜丝可乐。齐显和东北两个字格格不入,哈尔滨也同样与刻板印象中的东北迥然不同。如果让齐显来形容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他会说“浪漫”。哈尔滨的浪漫是可以直观见到、听到的,就如同中央大街两旁的欧式建筑,浮雕融进暖黄色壁灯,露台的栏杆积着雪,木门“吱嘎”响动、走出披袄的乐手,手指微动、呼吸之间,《我心永恒》从萨克斯的铜制喇叭管中流出,声音惬意温暖,像属于另一方向另一季节的海南夏天的海浪。它的浪漫更由浪漫以外的事物堆叠出来,像是带着稀奇古怪口音“everynightydreas|iseeyou,ifeelyou”的跟唱,像是一曲结束从某处忽然响起的掌声、和热情亲切但极度好笑的一声“优雅”,像是已经并不多见的一件军大衣,像是一座集古典主义巴洛克于一身的大楼它叫哈药六厂,让哈尔滨的浪漫有了区别于其他浪漫的独特色彩。一座钢铁铸就的雪花般的城市,冷硬又热情,偏偏这种矛盾感融合得浑然天成。居意游和齐显跟着说笑的人群沿街一路走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这种矛盾感就更突出、也更舒适。教堂前的人按簇划分,他俩没有加入任何一簇,只是坐在台阶上,目光漫无目的地飘动。一路上乐声都未停止,一声落下、一声又起。教堂前的两位戴着皮帽,一位吹萨克斯,一位拉手风琴,比之刚才又多了厚重。曲子从《多瑙河之波》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们看似有商有量,实则一位突然换曲、另一位赶忙跟上,急了还踹上一脚。略显随意的音乐仍收获回应,比如一旁的广场舞队,阿姨叔叔两两一组把它当作伴奏跳起交谊舞,舞步交替,各色棉袄在雪地里旋转,很可爱。当然也少不了约会的小情侣,居意游和齐显就是其中一对儿,以他们为圆心,卿卿我我的一对对扩散开来,看得人挺不好意思。“复苏”一词的含义大抵如此。他们至今仍旧觉得不可置信。2019年疫情开始,他们在高三语文答题卡上一遍又一遍写下的“时代是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进入大学一次又一次发下的防控通知,不断推迟的考试、抗议声中上线的门禁系统,居然就这么结束了。从无声无息开始、到无声无息结束。如果没有中途的经历,恐怕还能轻松地说三年“啪”自己消失了。就好像以后,除开端结局以外,也就记不住什么了。纷纷扬扬的各路消息出现一时,结束后就没人在意,失去什么、牺牲多少,在此刻必须画上休止符——起码在社会层面上。衰败的三年有衰败的,一场复苏里也有没能复苏的,答题卡上写得好,时代这粒灰的每次移动都会随机抽取幸运人士进行碾压,人力无法抵抗,抵抗了也只会换一拨人碾压。没被压死的人能全面放开、能松下那口气,但是长年的压抑消沉不受控制地显露、和幸存的欣喜混合,情绪不断放大,用极度外放的行为来完全覆盖负面的感受,成为“复苏”。教堂前的复苏也是如此。齐显怀里的姜丝可乐见底,他晃了晃瓶子,听见居意游问要不要一起去跳交谊舞,还没来得及回应,就被拽着混进阿姨叔叔中间。居意游假模假样鞠躬伸手进行邀请,形式走完就摸上齐显的手转圈。俩人都戴了手套,毛线厚实,于是不约而同地握得更紧些。可交谊舞只是优雅地轻轻搭手,小孩子围圈做游戏才会抓这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