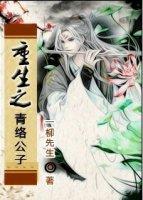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琳琅(清穿+空间)txt书包网 > 第197章 心潮(第1页)
第197章 心潮(第1页)
江离呆坐石榻,心绪如麻。若这不系舟的流民确系数十年前已丧生的峄州城百姓,那么自己过去多日来,难道是与亡魂相伴?这乍听来简直匪夷所思,可再回想自己来此处后的亲身感受,那些“人”的颠三倒四,来去无踪,不留半点气息,便又觉不像无稽之谈。何况若如他先前设想,有一众活人隐匿在此过活,这里却有足够的食物与蔽身之处么?他们真能做到永远不出不入,或即便出入也不被驻守之人发觉么?
他越想,越觉自己一向听闻,俱非活人动静,不禁身感恶寒。亏是那众亡魂从不曾加害于己,只这点聊可以为安慰。
峄州城与沧州相距数百里,峄州城的亡魂因何聚于此地?他在动念间便想到了原因:此地恰是己卯大火熄灭之处,那些人因己卯大火身死,大概与大火同来,却未与大火一同熄止,长久地徘徊于原地。这般想着,他眼前陡然浮现出渡僧桥畔如大雪纷落的余烬。那随着轻扬的火红尘尾骤亮,而后腾空远去的火光,承载的不就是逝者的神魂?而那送冥的习俗,正源自脚下这方奇异之地,大霜海。
大火星祭,既是为火神送行而举办的盛大典礼,也是丧生大火的千万亡魂的追荐仪式。仪式中大霜海祭司身着白绫,手持火尾翎羽,登丘行火尾舞。江离恍然而悟,大霜海之所以成为大火星祭无可替代的主祭场,不仅因是己卯大火的熄止之地,更是由于火止之后,那流离失所的千万亡魂便在此地开始了昼夜不息地徘徊!
亡魂的数量之多,以至于大祭司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送别。它们隐匿了痕迹,所以长久以来无人知晓。
他回想起虎丘天灯升起前夕那起伏的号角声。其时道平曾说,大霜海主祭以大祭司祭出招引之信作为开端,那吹响的号角,即是对那招引之信的效仿。眼下真正的招引之声已不言而喻,正是螭龙螺的螺声。自螺角吹响的一刻,大霜海中的亡魂即受到感召,乘着沙潮而来。不系舟,便是亡魂聚集之处。
江离的意念从万点余烬中冲出,流金粉屑的尽头现出零露的身影。螭龙螺原为她贴身之物,招引声也是她教所发,她了解不系舟中隐匿着亡魂,几等于握有与大祭司相同的权柄。螭龙螺乃无死生崖崖主所赠,那么为大霜海主祭的便是无死生崖。零露大费周折将自己送入不系舟,莫非是欲求助于无死生崖?可如今只剩自己,该怎么做?
真是只有自己么?他旋即自问。纵使这不系舟中的一切皆为虚幻,草叶包裹的食物是实,被盖在身上的草席是实,疗伤的绷带是实,递在手中的木杖是实,接住自己的手,温热的体温,耳畔的呼吸绝不会假,那个人!那个人不是无形的亡魂,而是有脉搏心跳,可以触碰到的人。
如今既教他知悉了不系舟的真相,那人的真容几已无法隐藏。他只等那人来当面对证。若事实如他所料,那人必定会再来。
想清楚后,江离走出岩洞去采集食物。虽没法捕鱼,但他先前已留意到了结有那种果实的植物所在,现下只需循路找去即可,若仍有余力,就去探路。如此一连过去几日,他已对岩洞周遭的情况了然于心,等待之人却始终没有现身。他只得继续埋头于眼下唯一能做之事,忍着焦急与忐忑,把余下交给耐心。
约莫是在第五日早上,那人来了。
那人在远处尚未走近时,江离便已然听到了,那杖端敲打地面之声鼓动着空气,扬起层层余波,下下带有回响。他坐于石榻,眼中世界被那声响震得一再发颤,表面却似不为所动。
“笃笃”声在岩洞外忽而止住,他的心跳随之顿了一下,而后剧烈地在耳中鼓噪起来,仿佛是那声响的延续。他看不见,但能肯定对方正在驻足望着自己。他回之以空乏内容的注目,缓缓站起了身。
俄顷,杖声再此响起,节奏依旧,他却从中嗅出了进退为难的不决。那人走至面前,又陷入了凝滞。他压下所有冲动,不发一言,只等那人作何表示。那人自然不出声,两人在沉默中对峙。
他听到对方压抑地抽了口气,极轻且颤,不可避免地牵带着杂音,仿佛能看到那人抽气时向后倾身的样子。他预感不好,担心对方会就此逃开,那人果就往后退了两步。他咬住槽牙,硬是不做一声,实因再明白不过,此刻说甚么都不如沉默有力。那人退后未立即离去,难料下一刻会销声匿迹,还是坦然相迎。
洞顶不时有水滴落,“哒哒”的响声,仿佛在为这场拉锯计时。江离眼眸灰黯,心中却已雪亮,忽觉盲眼有时胜过明目,可以更加不被干扰,而对方甚么都看得见,不知要为心绪平添多少波澜。又过不久,那人终是败下阵来,默默递过了木杖。
江离顺从地由木杖领出岩洞,朝着同一个方向,直走了一个时辰之久。裸露的岩地上的盐沙渐又多了起来,越走积得越厚,至半途岩石已被彻底覆没,到后半程时落脚开始松陷。风愈发干燥,显是回归到了盐沙之漠,皑皑霜海之中。
江离正寻思走了这许久,莫非已出了不系舟,就听突如其来一阵音浪,霎时把神魂从躯壳中击飞了大半!
竟是那潮声重回了耳畔。
他不由顿住了脚步,面对天边神情怔忪。潮声就在前方,不会听错,那绝非渤海水涌,或风声作怪,委实是那沙雾狂潮卷土重来!他一惊非可,急将木杖向后扯道:“快走,休再向前!”不想木杖纹丝未动,自己反被带得向前跌了半步。他急道:“你做甚么?听不到那潮声……”话说一半,忽就噎住了。
那人怎可能听不到?难道那潮涌之处,正是此行的目的?
那人见他哽住,便将杖端微微抬了两下。江离问:“你要带我过去?”手中杖端又是一抬。江离强稳住心神,忽想到一事,心中陡亮,便点头向前迈开步去。
两人向着潮声继续走了将近一顿饭工夫,风声越发凌厉,空气浑浊万分,盐沙击面,渐成风暴之势,那沙潮奔涌声更是变得可怖。江离渐觉难支,脸上铺满沙尘,衣袖被风吹得噼啪狂响,如有鸟群在周身振翅。
沙暴偶有间歇,风力有瞬时的减弱,他惊觉振翅之声竟未间断。四周一旦稍静,那声音便更加明显,似乎来自高处。难道此间真有鸟群飞过?这怪念头只在他脑中一转,旋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手掌忽被木杖一顶,他立刻依示意止了步子。一经停下,才知沙潮已近在咫尺。
“到了么?”噪声巨大,他不得不大喊出声。
杖端一抬。
他以手扯住半张脸,仰起头对着沙潮的方向:“……你带我来这,莫非是想告诉我,是它阻了出去的路?”
杖端又是一抬。
他想了想道:“你想和我解释,你不是不愿送信,而是不能?”
杖端第三次抬起。
江离闻言低笑一声,忽将遮脸的手放下,露出无神的双眼紧盯着那人,就好像能看得到对方一样,如此问道:“我有一法,或可驱散沙潮,不知你愿不愿一试?”言毕他不等对方反应,当即甩开木杖,手在腰间一抹。微光闪闪,他已将螭龙螺贴至唇边,下一瞬就要将之吹响!
只是还未来得及吸进半口气,已有迅风扑面,是对方从对面急逼过来。江离见机利落地将螺递出,竟是毫无犹豫。那人反应奇快,见状立知他吹螺是诈,急忙缩手,却及不上他早有准备。慢了半瞬,手腕即被江离另一手捉去。
那人情急,下意识要甩手挣脱,说时迟那时快,江离“啊”一声叫出来,作出痛楚神色,那人便如瞬间冻住一般,动作骤止。江离趁机扑上,一把将那人抱在了怀中。
“呼!”那人的发丝被呼啸的狂风吹起,顷刻间如墨汁般泼在江离身上。她好像惊惶无比,像被滚油烫到似地不住用双手推拒着江离的肩膀和上臂,却又不敢真的使力,呼吸粗重,气声沙哑如杂泥沙。
江离紧抱不放,感到她胸口起伏,心跳如擂,更加不疑,于是出声叫道:“零露!”
那人浑身俱是一颤,僵住不能动弹。
江离趁势将手摸向她颌下,所触之处皮翻肉绽,自刎留下的创口尚未愈合。他一阵心惊,当即将她抱得更紧。“你果然没死,”他像怕她听不到似地,垂下头道,“别再藏了,我知道是你了,我知道……”然后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有顷,他感到抓着自己上臂的手渐渐软垂,对方似被这句话彻底击溃,就此放弃了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