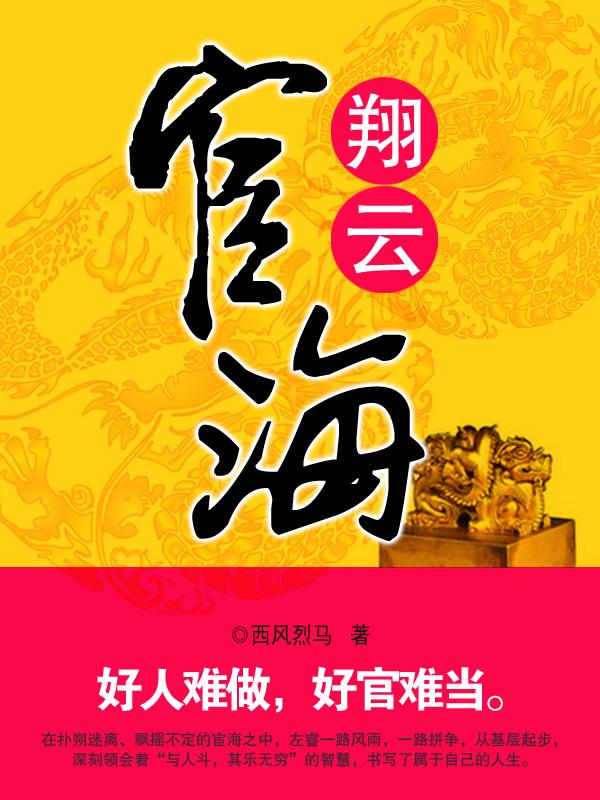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绝对掠夺免费阅读笔趣阁 > 第206章 无药可救(第2页)
第206章 无药可救(第2页)
它能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独狂却不能。
独狂的头还在疼。
他一身的骨头和肉,都还在疼。
要命得疼。
比这还要糟糕一些的是,他身上的衣服也已变得破烂不堪。
有着彭恶掌力的震摧,和泥土的摩擦,独狂身上的衣服又怎能完好得了?
在如今看来,他完全就是一付土头土脸,浑身是伤,外加衣不蔽体的样子。
土头土脸倒也不要紧,找个地方洗洗也就干净了。
浑身是伤亦不要紧,受伤并不可耻。
但衣不蔽体,还怎生去见人?
独狂沉吟了下,也走进了树林。
树林又深又密,林中的树木亦是又高又大,却好象这林子里就不可能会长出衣服来。
独狂往深处行了老半天,正不知该如何设法,就看见了块巨石。
这块巨石的质地和形状,倒也并无甚么奇异,但明显就有些被翻动过的新鲜痕迹。
是谁刚来到了这片树林,翻动过这块石头?
独狂盯着这块石头瞧了会,眉头忽然动了动,走上前去,试着用力去推动。
这块巨石怕少说也有几万斤,他实就不知自己能否推得动。
特别是在此刻全身都疼得要命的情况下。
结果却是出乎意料得好,他并没有费上太大的力,就将这块巨石推出了数尺。
巨石旁移,下面赫然露出了个颇大的洞穴,洞内也不知有多深。
独狂站在洞口探头向里面望了望,未再多想,人已走了下去。
入到洞中,行出几步,他一考虑,又回到了洞口,从下面尽力去托动巨石,将洞口重新封了起来。
洞内本就不见明亮,洞口这一被封,里面顿时就黑暗了起来,幸好依独狂现今的目力,静立了会后,仔细去瞧,也能勉强分辨出几丈远近的一些大概事物。
他且细望,且缓走,足足行了上百里,也不见走到尽头,除了发现这洞中并无岔道,亦是弯弯曲曲之外,更是压根就没有瞧见什么东西。
这样子,独狂倒不失望,却是忍不住停了下来。
他正就不想再这样走下去了。
哪知一声尖尖的吱叫声,忽地自前面的弯洞中响起,好险没把他的心给吓得跳出来。
独狂苦笑了下,定下心来瞧去,就发现前面的弯洞中,有双眼睛正也在看着他。
这双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表情,象是充满了惊怕,但似乎就不是双属于人类的眼睛。
隐在这双眼睛后面的身体,听其声,观其形,仿佛就是只老鼠。
一只其大如虎的老鼠。
独狂迎着这双眼睛,走了过去。
这双眼睛之意更见畏缩,象是随时都在准备夺路而逃。
但好象它就有点认识独狂,亦似乎它很清楚独狂根本就奈何不了它,这同时它大概也感觉到了独狂对它并无甚么恶意,所以终是未去逃窜,仅是警惕地打量着独狂,小心提防着他的靠近。
近行到了丈外,独狂总算看清了这双眼睛真是属于一只老鼠的眼睛。
一只身上长满了长毛,其大如虎的老鼠。
不过独狂就无法肯定这只老鼠便是他骑坐过,并将他摔了一跤的那只老鼠。
只因天下的老鼠几乎长得都是一个样,除了能从大小、肥瘦去做出些判断外,实难区分得出它们谁是谁来。
而这天下看来大小相似,肥瘦差不多的老鼠,本又何止千万只?
倘若这地洞里没有别的长毛老鼠,这只长毛老鼠应该十有**就是将他从奴隶中的那个地洞里驮出来的那只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