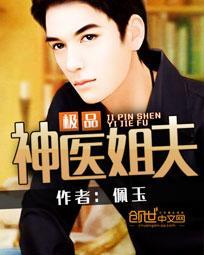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我的姐夫全文免费阅读江深 > 第五十六章 冲突(第1页)
第五十六章 冲突(第1页)
“张鹤龄,尔敢,尔敢……”
驴市百户所门前,李梦阳怒着一张脸,手遥遥的指着张鹤龄,恨声喝道。
只见张鹤龄手持马鞭,铁着一张脸,冷酷的看着身前的这些士子们。没人会怀疑,只要有人上前,张鹤龄便会给他送上两鞭子。
刚刚的那一个士子,此时满脸是血,正是最好的榜样,一时间,来找事的士子们,气势都弱了几分。
不过,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李梦阳和他身边一人的怒声喝骂,再次挑起了他们的情绪,比之前还要来的凶猛。
大概只有士子之间偶有摩擦,面对其他群体,即便是那些数的上名号的朝堂命官,他们也未曾吃过亏。如今,竟然被一外戚,一个锦衣卫打了,甚至让他们一时气弱,这内外的羞辱何其盛也。
一时间所有人都振发了精神,甚至狰狞着面孔,如同义无反顾的战士一般,向着张鹤龄冲锋而去。皆是要冲上去找张鹤龄算账。
张海、邢朝,孙继和一众锦衣卫,赶忙的挡了过去,双方在百户所门前猛然的撞在了一起。
冲突升级了!
张鹤龄退了一步,手一挥命令道:“张海、邢朝,动手,抓人!”
张鹤龄早就想动手了,之前只有4个人,他这才和对方周旋,使得放开百户所的门前。
每个百户两个总旗,加上大小军官,大致100人出头,平时一队执勤,一队留守,即便如今锦衣卫有些空额,但百户所内的锦衣卫也不会少于三四十人。
能被二三十人堵着门,盖因锦衣卫不敢动手。也是李梦阳聪明,未曾真个带人冲进去,否则即便锦衣卫不敢动手,也得动手。
现如今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不敢动手也要动手,冲突已起,上官的命令已下,必须无条件执行。昨日这位伯爵爷带着兵马司立的威可还在呢,别说外人,即便兵马司兵丁,因办事不利,打的革的,已二三十人,他们可不想放弃这身衣服。
张海也是一声高喝,随之下令,跟着自己也冲了上去。
场面一时有些混乱,锦衣卫们动手是没错,但可不敢动兵器,而那些士子们似乎脑袋彻底发热了,完全不管不管,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嘴里还在喝骂着,不停的给自己给同伴鼓劲。一时间倒没能拿的下来。
张鹤龄很不满意,不满意校尉们的表现,也不满意那个李梦阳没上去动手,甚至还往后退了退,撤开了些距离。锦衣卫看李梦阳退后,他们也没追,只对付着其他士子。
他盯着李梦阳,喝道:“李梦阳,你串联监生、士子,先是妄议朝政,围堵锦衣卫官署,冲撞朝廷命官,是为一罪。其后,更裹挟士人肆意妄为,妄图干扰朝廷司法公正,是为二罪。最后,更诋毁圣上,辱人先人,罪大恶极,尔等枉读圣贤书。”
李梦阳心里也是冒火,张鹤龄的表现超出他的预料。想两年前,他当街挥鞭,差点打掉了张家兄弟的门牙,也未曾见他敢反抗过。即便他已知昨日巡城御史吴尚被踢了一脚的事,但他也未曾想过张鹤龄敢动手,甚至命令锦衣卫抓人。
不过,此刻他依然保持着理智,未曾和锦衣卫上去冲突,只是在一边沉痛的高声喝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等士人只是为无辜之人讨个公道,却被尔污为罪大恶极。士可杀不可辱,尔枉顾法纪在先,打人在后,现强令锦衣卫抓捕士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等岂容你这奸佞再祸乱天下!”
说完,他的手高高举起,似乎是要准备冲上去一般,那些士子们被这一鼓动,更加的热血沸腾了,仿佛是在做着无比正义之事。
有些身子稍健壮些的士子,和锦衣卫空手心虚的抓人动作竟搏了个不相上下,甚至,一名手快的士子,把手都伸到了锦衣卫腰间的佩刀上,真真的是豁出去的架势了。
张鹤龄越看越看不下去,三十多个校尉、力士,还有穿着飞鱼服的总旗小旗,竟然连张海也似乎放不开手脚。如此情状,让他这个掌事的头情何以堪。
他心中知道,如今这世道,当兵的遇到文人士子,先天上了矮了几分气势。即便昨日让他们打总宪的儿子他们也能硬着头皮上,因为,戴盛算不上正经士子,总宪即便报复,那也只是个人的。
但今日面对这些普通身份的士子却偏偏放不开,因为,能穿儒衫的,皆是有功名之人,士农工商,几十上百年养成的士人优越,此思想已深入人心。以前锦衣卫还行,但牟斌规范了十几年,那套仁厚也慢慢的侵蚀到锦衣卫之中。
以前如何他管不着,包括现下的其他人他也管不着,但在他的地盘上,决不允许有理也矮三分的情况发生,谁来也不行。
念罢,他本着脸,沉声喝道:“五息之内,若是还拿不下这些人,尔等全部卸甲回去种田吧,朝廷不需要尔等这样的废物,锦衣卫不需要,我张鹤龄更不需要。”
三十多个锦衣卫,被张鹤龄的一声喝,喝的脸上一阵精彩。
不但是自尊心,更是上官话里那份不容置疑,张海更是受不了,他感觉,几日来殷勤靠拢前后忙活的效果,似乎正在悄悄的离去,他心里愤恨。
“上,哪个兔崽子敢再手软,伯爷仁慈不收拾他,老子也先收拾了他!”
他发了狠,举起刀鞘,一个侧拍,直把一名上前的士子拍翻在地,怒道:“给我抓,若是有人再敢反抗,给我用刀鞘砸,打死了,我张海顶着!”
“上!”
一声声的怒吼跟着而上,校尉们也是不管了。
其实事情真的很简单,几十个常年玩刀的人,即便是如今京城的锦衣卫没见过太多打战的阵仗,但也不是一群书生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