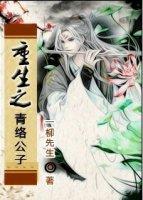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和教授互撩的日子 免费阅读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这可不是道歉该有的态度。谢宜珩抱着手臂,冷冷地看着他,暗自感叹着自己地投诉信居然只换了这么一个阴阳怪气的回复。
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是头一次,她站在一边,无形之中拉开了和爱德华的距离,漠然地说:“我们确实来不及。莱斯利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您也该考虑他的身体状况。”
爱德华摘了眼镜,目光锐利得像把解刨刀,将她开膛破肚:“我也七十多岁了。”
一码归一码,他平时脾气差爱骂人,但是绝对严于律己。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天天工作到午夜十二点,脸色差得不用化妆就能去扮演撒旦。
爱德华碰了个钉子,难得没发货,叹了口气。他的声音疲倦又苍老:“路易莎,我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寻找引力波这件事上了,但是它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回应。”
他闭着眼,微微仰着头,说话的声音很轻,却又带着不可忽视的威严:“尼泊尔发生了地震,南极的冰川在融化,太平洋的海水拍击着礁石,城市的街道上汽车在鸣笛。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声音,我们却要寻找一个质子直径千分之一的震动。”
谢宜珩顿了顿,说:“我知道。”
“你不是科研工作者,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尽快完成噪声识别。”爱德华抿着唇,死死地盯着她:“路易莎,人们很难对真理保持永恒的热情,但至少我们要怀有敬畏。”
最后一句话他说得虔诚又悲怆,像是一个一无所获的信徒跪拜在上帝脚下,一遍又一遍不胜其烦地低声祈祷。谢宜珩把手插进口袋里,对他说:“我不接受您的道歉,但是我会完成我的本职工作。”
爱德华最后也没说什么,又重新带上了眼镜,一个人默默地走了。他的脚步声很沉重,回荡在空空的走廊里,像是教堂黄昏时分的钟声,庄严里满溢着寂寥。
…
晚上的时候谢宜珩又开始了无止境的加班工作。她和康妮一人霸占着桌子的一侧,台灯的光线昏黄,打印好的文献堆了满桌。
亨利看过了她那篇关于卡尔曼滤波的报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谢宜珩逐条对应,照单全收,一边改一边给老教授发了封邮件。
“爱德华和康妮都好恐怖,天天工作到半夜,喝咖啡如流水,简直是为了引力波燃烧生命。”
远在加州亨利一看到这封邮件,高兴得直接从病床上蹦起来,连连感叹路易莎开窍了,赶紧回了一封邮件:“这些教授都是很了不起的人,莱斯利上大学的时候,为了看书经常连饭都忘了吃。”
这么多勤奋标兵,亨利偏偏挑了个定义域外的选项来答题。
谢宜珩:“莱斯利每天和康妮约会,八点起床八点睡觉,到实验室比我还晚。”
亨利怒了:“要尊敬计算机科学家!”
谢宜珩看着那个大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突然想到了中午裴彻的那句“以后就算了”,呼吸停了一下。
怎么会算呢。谢宜珩自嘲地笑,摇了摇头,把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赶出脑海,继续埋头工作。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康妮终于回来了。意大利女士一只手抱着另一束崭新的红玫瑰,另一只拿着一沓惨白的打印纸,满面笑容地对她说:“晚上好,路易莎。这是莱斯利写完的方案,他让我帮忙带过来的,希望你们工作顺利。”
谢宜珩向康妮说了谢谢,接过资料,心情也和打印纸一样惨白。莱斯利的摘要写得很清楚,谢宜珩只略略看了几眼,就把内容看了个大概,问道:“那我明天来您的办公室找您吗?”
噪声识别的第二部分就是卡尔曼滤波,通过这种高效率的方式,干涉仪内部的悬挂线因热力因素所产生的震动会被滤除,进一步提高了ligo的灵敏度。
康妮极擅长精密测量,反射镜和悬挂线的悬挂位置就是她定下来的。为了达到爱德华的要求,谢宜珩和莱斯利必须要根据具体的内部情况来制定方案,所以要和康妮对接。
康妮明白了她的意思,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找爱德华吧,他不再让我插手内部结构了。”
谢宜珩和康妮短暂地对视了一瞬,她们仿佛面对着的都是镜子,目光里的情绪一模一样。
她们不理解甚至恼怒爱德华莫名其妙的傲慢,但是不会否认这位老人对于追寻真理的执着。
谢宜珩坐回了桌子前,发邮件问爱德华明天什么时候有空。过了好一会儿,邮箱的图标上才出现了一个姗姗来迟的小红点。
爱德华:“你明天可以去找劳伦斯。你们在加州理工的时候不就已经讨论出初步方案了吗?现在按照具体情况再调整一下好了。”
谢宜珩被踢皮球一样的踢了一圈,最后奇怪地回到了裴彻那里,她有点恼火,键盘被摁得噼里啪啦响。
写邮件的抬头的时候,谢宜珩纠结得差点咬指甲。称呼是个问题,用“亲爱的劳伦斯”则十分矫揉做作,而叫“劳伦斯先生”又有点刻意营造的骄矜。
谢宜珩左思右想,甚至还特地翻出了之前裴彻写给她的邮件的抬头——一个简简单单的“路易莎”。
单单一个“劳伦斯”好像爱德华趾高气扬地在办公室里喊人的样子。
一个称呼她纠结了五分钟,最后当机立断,直接写了个“劳伦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