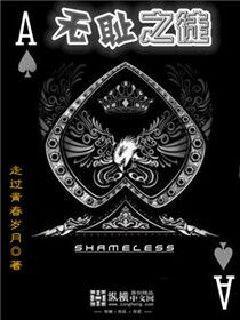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神州1855TXT > 第30章 君向潇湘我向秦(第3页)
第30章 君向潇湘我向秦(第3页)
“中堂,就算冯天养真的存心造反,此时开战,船厂一旦毁坏,如何与朝廷交代?船厂乃与英人合建,一旦损坏,英人借此滋事,又如何应对?”
赵寒枫言辞恳切,叶名琛虽然一开始听得有些不耐,但听到船厂之后却猛地一怔,然后慢慢冷静下来。
“中堂,立光言之有理,船厂不容有失,即便冯天养真有反心,也当徐徐图之,请中堂息怒!”
柏贵作为船厂政绩的共同受益人,此刻也是猛然醒悟,出言劝谏。
“请中堂息怒!”
柏贵出言后,谈元益为首、仲喆、毕澄三人先后拱手出言附和。
其中仲喆和毕澄二人虽然心有不甘,但也知道叶名琛已经投鼠忌器,再拱火只会引火烧身,只得无可奈何的随着谈元益拱手。
“是本督怒火攻心了,立光此言实乃老成谋国之论!”
叶名琛借坡下驴,随后又好言安抚了刚才被自己怒斥的赵寒枫一番,环视众人一圈,将柏贵和赵寒枫留下,然后让其他人都退下。
“雨田兄,省城舆论纷纷,不利于此事处置,本督不好出面,劳烦雨田兄以巡抚衙门之名,召集士绅清流消解流言,此事可由仲喆和毕澄二人带头做起。”
“中堂放心,下官省得。”
柏贵知道这事只有他出面最好,且此事他和叶名琛本就一体,于是慨然应下。
“立光兄,即刻调那两千绿营去惠州协防,所有设立工事一并拆毁,然后致函冯天养,责令其恢复道路,撤回团练,此外一个字也不要问,更不许私下写信与他。”
叶名琛叹息一声,随即安排起赵寒枫将那两千绿营调离。
赵寒枫说的对,无论冯天养是真反假反,只要一打起来,其人势必挟船厂自保,自己到时候才是真的投鼠忌器,进退维谷。
只要这把火没有真的烧起来,一切就都还好处置。
将化解舆论和停止对峙两番事情一并安排完。叶名琛思量半晌,取了一份文书,换了一身便服,乘着一顶不显眼的小轿来到苏峻堂家中。
且说,自那日苏峻堂拒绝写信之后,其人便已留印于按察司大堂,然后带着妻女搬到了城中的别院。
而此院也立即被总督府派人看管起来,一应来往人员和物品均被严格管控,就连为苏家出门买菜的老仆进出也要被仔细翻检。
推开院门之时,苏峻堂正带着他那年方十三的女儿苏瑀桐在小院空地上开垦一块小菜园。
只是苏峻堂平日少干农活,开垦的菜行又歪又斜,不成方圆不说,两人还都是蓬头垢面。
叶名琛原本进门后颇有些踌躇之状,见此情形反而轻松下来,将苏瑀桐手中锄头接过,然后亲力亲为,和苏峻堂一起将那菜园子修整成方正模样。
两人各自洗了把脸,在院中凉亭坐着歇息,苏瑀桐乖巧的将茶水呈上,然后回到房间帮母亲准备饭菜。
“瑀桐今年十三了吧,快要及笄了,当年来广州时才不过七八岁,一晃五六年过去了。”
叶名琛看着乖巧懂事的苏瑀桐,不禁感慨。
“时光如梭,昆臣兄,你我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苏峻堂也是感慨,他和叶名琛三十岁便相知相扶,一晃二十余年,对方年轻时面容犹在脑海,再和如今一对比,真可谓时光如梭。
“圣人五十知天命,你我皆俗人,五十虽至,天命难知啊。”
叶名琛感慨一番,却也不再拐弯,先是谈起了今日在总督府发生的事情,然后开口。
“新安之事如何收尾,平泉兄静居这几日,可曾考虑?”
“不瞒吾兄,终日思虑此事,未有良策。”
苏峻堂叹息一口气,表面上的分歧容易拟合,毕竟双方并未真的打起来,但关键的是冯天养和叶名琛经历此事,彼此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绝无单方让步的可能。
若是寻常县令被误解或是犯了错,别的不说,能来总督府陈情自述一番已是格外恩典,但冯天养经此一事,岂敢轻易离开新安?
“总得须根本督一个台阶下,冯天养要是不愿来,写一份文书自述其过,贬官半级,将其妻子叔父送到按察司衙门暂住如何?”
叶名琛试探着开出条件。
苏峻堂闻言颇有些惊疑之色,这个条件太过宽松了,近乎谋反的事情被轻轻揭过不说,就连自己已经决心放弃的按察使官位也保住了。
以当前如此凶猛之舆论态势,叶名琛如此处置付出代价必然不小。
“吾兄如此宽容,想必还有其他条件吧?”
苏峻堂试探着开口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