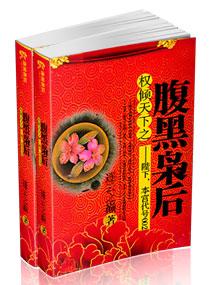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穿成冲喜新娘txt > 第174章(第1页)
第174章(第1页)
长公主府非但机关重重,且暗藏数位高手,能打探到禅院也是石乔的一个手下拼死得到的消息。
江司匀神色焦虑,又问道:“可曾绘制了长公主府的地图?”
“有,但长公主府内布满了阵法,有些地方也许随时会挪动位置。”
即便是石乔,略懂一些阵法也差点折在里面。
古滇皇族不一样,他们善用蛊术,完全可以操控公主府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高手。
江司匀揉揉眉心:“拿来给我看吧。”
御书房里,曹斌又在跟钟亭深干架。好在这个时候,房间里只有这二人,故此外人也不得而知。
曹斌了然无趣的将折子扔到钟亭深怀里:“你来看看,张庭是不是疯了,竟然夸你?我没看错吧?”
张庭乃是翰林院编修,同时还兼着御史一职,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是丞相党的铁杆,对丞相葛洪言听计从,原本是打击太师党的急行军,可最近竟破天荒的频频上折子夸赞钟太师为官清廉,乃是国之柱石。
钟亭深瞪着眼睛不忿道:“怎么了,还不许别人夸我了?这么多年我为了苍蓝忍辱负重,别人夸我两句怎么了?”
曹斌指了指窗下的一大摞奏折:“可就算是夸你,也不该是张庭,你自己看看这段时间,除了葛洪那老穷酸没有上折子吹捧你,他下面的大小官员,哪个不是脑子进水了,逢你必夸,这不对劲啊。”
原本是不死不休的两党,竟然莫名其妙的握手言和,这转变大的让曹斌每次看折子都诡异的嘬牙花子。
钟亭深喝了一口茶,抬起眼皮傲娇的说道:“兴许是那帮子小穷酸脑袋开窍了,我还觉得夸得不够。”
曹斌酸溜溜的说道:“得了吧,兴许葛洪那个老东西变换方法了,想要捧杀你,你瞅瞅,现在整个朝廷里都像你的一言堂了。”
钟亭深冷哼几声:“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自打我坐上了太师之位,不就等着这一日吗?那些小穷酸们夸我也好,骂我也罢,左右不就是给你递刀子吗?”他伸着脖子说道:“来来来,赶紧砍了我,这千人唾万人骂的日子我也是过够了!”
虽然这话半真半假,但钟亭深何尝不知这也是事实。
“你闹什么闹?你老东西就知道拿这个威胁我!”曹斌捡起一本奏折扔了过去。
钟亭深睥了曹斌两眼:“现在不威胁你,等你两腿一蹬,你们家的那个小木头和葛洪这个老穷酸还不得吃了我?不干了,坚决不干了!”
他和曹斌均已暮年,早晚要退到幕后的,他虽为曹斌的刀,但也是暗刀,这些年来即便不是他出手,那些仗着他做靠山的下官们没少为非作歹,一旦曹斌驾崩,他死了不可怕,但也得替自家那个臭小子好好筹谋一番。
曹斌气的手指颤抖:“钟亭深,要不是看在这么多年你为苍蓝殚精竭虑的份上,就凭你刚刚的话,信不信我离开让人砍了你?”
钟亭深起身对着曹斌行了一礼:“既然皇上有此旨意,那我现在便回家自裁以谢天下”
说完,便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
曹斌气的脸红脖子粗的,好一会这才盯着钟亭深的背影嘟囔道:“果然,自从葛洪那个老穷酸告病之后,你也不可爱了,弄的朕都没戏可看了……”
帝王之术讲究制衡,而钟亭深和葛洪就是两枚最大的棋子,寻常时候,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他这个冷眼旁观的人看来,何尝不是一场大戏。
这么多年他也知道自己亏欠钟亭深良多,可为了朝政为了苍蓝他只能选择牺牲他。
钟亭深的忧虑他同样看在眼里,不由得开始琢磨小六和钟鸣的婚事还是就此作罢。
刚刚走出宫门,太师府的人就传来了消息,钟鸣回家了。
钟亭深冷哼一声,嘴上骂着小孽障,但还是弃用轿子,反而选择骑马回家了。
一进门,就见钟鸣正抱着一只烧鸡大快朵颐,吃的毫无形象。
钟亭深没好气的一巴掌拍在了他后脑勺上:“臭小子,你不是不回来了吗?谁让你吃我家的烧鸡的?”
钟鸣揉着脑袋笑嘻嘻的回头:“爹,他们说你进宫了,我还想吃了东西就去找你呢。”
钟亭深将桌上的一盘花生米扯了过来,边吃边说:“你小子在外面过的风生水起,我听说易水城的百姓还给了你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名头,找我做什么?”
钟鸣捏捏鼻子打趣道:“呀,这烧鸡没放醋怎么这么酸啊,爹,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名声比你好,所以嫉妒我了?”
钟亭深嚼着花生米斜了钟鸣两眼:“你爹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用得着嫉妒你那芝麻绿豆小的县官?”
“爹,你别不服气了,现在我出门人家在背后就得竖大拇指,您,呵呵,不竖倒拇指就不错了。”
“越说越没规矩!”钟亭深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眼底满是欣慰之色。
前些时日,朝堂之上丞相党的官员夸赞易水城匪祸被剿灭,百姓生活安定了下来,虽然暗讽钟鸣和他不是一条心,忠奸迥异,但还是让他心里比喝了蜜还要甜。
若是有选择,哪个当官的不愿意成为百姓口中的青天呢?
想起怀中的东西,钟鸣又收敛了嬉笑之色,郑重的盯着钟亭深。他咽了咽口水,艰难的说道:“爹,我可能给你惹来了一个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