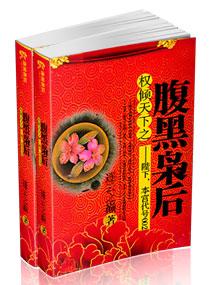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魔法界的研究 > 第84章第84章(第1页)
第84章第84章(第1页)
“这么说起来,”德拉科喃喃地说,“我倒是挺羡慕你的。”
伊诺克觉得自己好像明白德拉科是什么意思,他又想起来那个他自己也不敢往下细想的类似阴谋论的东西了。
“这我就不明白了,”他说,假装自己并没有往那个方向猜,“你一毕业就结了婚,没错过一点儿可以跟她一起度过的时间。要说也该是我羡慕你才对。”
“我很难怀疑她其实并不想我以为的那样需要我。”德拉科说,“就好像——就好像她没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那我就更没什么可被你羡慕的了,”伊诺克说,最后给他展示了一次那枚项链坠然后小心地收回了口袋里,“她也一样。”
“不一样。”德拉科反对得很认真,“格林格拉斯离了你可能确实还是照样过,但她对你就跟被灌了迷情剂似的。水蓝儿不一样:她不仅没多需要我,而且喜欢我也没有我喜欢她那么多。”
“她还是挺喜欢你的。”伊诺克说。德拉科对阿斯塔的评价一方面让他觉得算是冒犯,一方面又让他的自信心像是被恭维了似的有点儿膨胀起来。他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反应,就假装没听见。
“这不公平。”德拉科说着屈起膝用胳膊肘笼住,然后有些沮丧地把他的尖下巴放在双膝之间,“她随便干点儿什么——甚至是她只要一呼一吸都能牵动我全部的情绪。但是我对她来说就没那么重要。”
这话有点儿熟悉;这个动作也是。上次伊诺克给人解决这类情感问题还是在十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对她说了很多开导的话。不过,在十五年后的今天,面对着这个方方面面都比他更出色、跟“弱势”这样的词挂不上钩的男人,他不是很想说。
“唔,德拉科,”他含混道,“你知道,人不能只为别人活着。”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真是很好笑。”
“这么多年了,我也总得学会点儿东西嘛。”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也很好笑。”德拉科说,并且真的笑了,“我觉得你一点儿也没变。”
他好像立刻就从刚才那种伤感情绪中缓过来了,而且笑得很得意,于是伊诺克决定说些让他不舒服的话。“又不是我自己想原地踏步。”他故意轻快地说,“要不是你我就当上主治疗师了。”
好像奏效了,德拉科的笑有点儿发僵。不过他转了转眼珠子,又立刻把话题拐回对方身上。
“但你的确还是跟以前一样优柔寡断。”德拉科说,“不然你早该拿下她了。说真的——格林格拉斯那家伙——我不觉得她能等你太久。”
伊诺克跟他对视了一会儿,最终决定相信德拉科说这话是认真的。
“不,”于是他谨慎地说,“我有个计划。”
“你最好是。”德拉科说。说完他就又把头扭过去了,伊诺克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挺感动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关心。”他说,“喂,听见了吗?我说‘谢谢’了。你的耳朵最好不是个摆设。”
德拉科没回过头来,但抬了抬下巴表示听见了。
“你们这些会做计划的人真的很烦人,”他说,“水蓝儿就是这样。自以为做什么都是为了别人好,就什么都不说,非得自己悄默声地把什么都干了。她每天跟我说那么多话,全是让我如何如何做,一点儿也不让我知道她在做什么。”
伊诺克一边听他说话一边谦虚地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做了类似的让阿斯塔不舒服的事。做了计划而不告诉对方,这确实有:他很能理解水蓝儿,计划是不能告诉被包含在计划里的人的,尤其是那个人对这个计划的实现很重要的时候。诚然,这有时会让他暴露在让对方失去耐心的风险下(他的几任前女友都不太受得了),但是——至少在计划完成之后——阿斯塔似乎还挺喜欢他这一点。至于像水蓝儿那样强势地发号施令,阿斯塔肯定会很反感,但他确信自己没那个习惯。
“她可能就是很看重你才会不告诉你。”伊诺克认真地说,“你得有点儿耐心。”
德拉科显得有点儿纠结,伊诺克觉得自己知道他在想什么:德拉科一方面想呛一句“‘有点儿耐心’,那换你来忍她试试?”,一方面又觉得伊诺克不应该有这个机会,自己坚决不能给他一丁点儿可乘之机。
“换句话说,”伊诺克见他不说话就补了一句,“那不也是她让你喜欢的一部分吗?”
德拉科没说话。伊诺克估计他不是在思考那到底是不是就是清楚地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而不愿意说。
“不过这事我确实一直挺好奇的,”伊诺克试探着又说,“你到底是喜欢她哪一点?”
“你还好奇这种事?”德拉科又笑了,“真无聊啊,怪不得你会跟瓦妮莎凑到一块去。真的,伊诺克,你应该反思反思为什么从小到大你的女性朋友都远多于男性的。”
那你也应该反思反思,伊诺克想,为什么你不认识比我这个有一群女性朋友的家伙更让你觉得适合离家出走之后躲到他家里的人?但他知道德拉科是故意想岔开话题,就没接着这个话头儿说下去。
“那你们俩到底是灵魂上的契合,”他放慢了语速,“还是——呃,原始的性冲动——”
“什么灵魂,”德拉科嬉皮笑脸地打断了他,“咱们斯莱特林不谈那些虚的。”
显然他并不忌讳承认水蓝儿的□□对他来说相当具有吸引力;但是伊诺克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真正想问的那一点上,并不准备让德拉科这么轻飘飘地混过去。而且,显而易见地,德拉科本来完全可以强硬地要求他结束这个话题,但他没有。伊诺克由此判断德拉科其实同样愿意讨论:大概他也挺希望有人愿意分享他的憋屈,而他面前显然就是这么一个挺合适的不会嘲笑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