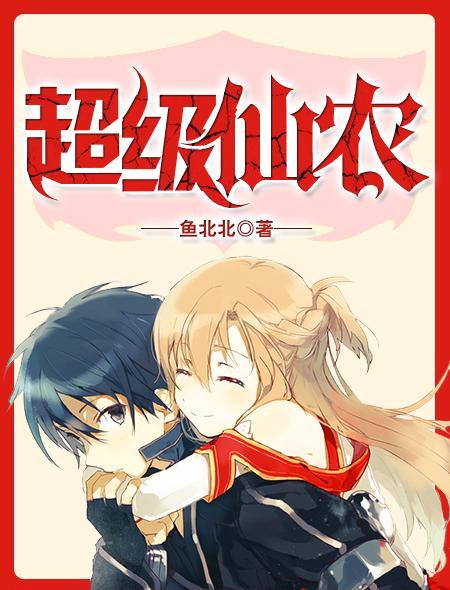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樱桃痣by > 第61章 殷姚你别走(第5页)
第61章 殷姚你别走(第5页)
但政迟听着,只觉得无尽的绝望。
这种绝望让他清醒。
他觉得自己该解释什么,迟到太久也好,苍白无力也好,他想告诉殷姚,“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越遥。”
“我知道。”
殷姚再一次回应他,“我不在乎。”
殷姚累极了,他缓缓闭上眼,很快,不过一会儿,就安静地睡着了。
政迟默默在殷姚身边很久。
月亮沉了下去,天色昏沉发亮,屋内很暗,殷姚翻了个身,闭着眼睛,呼吸平稳,眉间舒展着,睡得倒十分安心。
虽然也容易被弄醒,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不安分,那时候常做噩梦,不知道梦到了什么,总是不安地发着抖,惊醒后就往他怀里钻,直到重新睡着为止。
快要日出了。
“老板。”
朗九知道规矩,没有敲门,步伐极轻地过来,见政迟俯身轻吻了一下殷姚的额头,才缓缓起身。
“什么事。出去说。”
“……是。”
朗九的表情意外的严肃,额头上有冷汗不断冒出,整个人的状态十分奇怪。
去了廊外,更是不安,他脸色发青地抿着唇,因为僵硬手臂迸出青筋血管。
“老板,节哀。陈叔的事……”
“不必说这些。”
一日一夜的蹉跎,政迟难掩疲色,挥了挥手,淡淡问,“怎么了。”
“……母盘,不见了。”
朗九死死攥着拳,自知有负所托,艰难道,“是我无能。”
许久,政迟问,“怎么会不见。”
“不清楚。”
“不清楚?”
朗九僵硬道,“是。”
他说,“您回国办事的这段时间,母盘一直都是由我看管的,摄像监控都没有录到任何外人闯入。只有……”
只有一种可能,不是失窃,而是由内部送出去的。
政迟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闭了闭眼,说,“你想说什么。”
朗九干涩地咽了下,目光不经意地撇了眼殷姚卧室的门。
他脸色微妙,不自在极了,万般纠结后,却还是硬着头皮,开口道,“这屋子里,只有一个人,房间里没有监控。”
也只有一个人,想去哪里,都没人敢拦着。
“老板,也不一定,”他磕磕巴巴地说,“只能说,比较大的可能,是殷姚,在您不在的时候……”
私自将母盘……窃走了。
说罢,朗九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窥探政迟的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