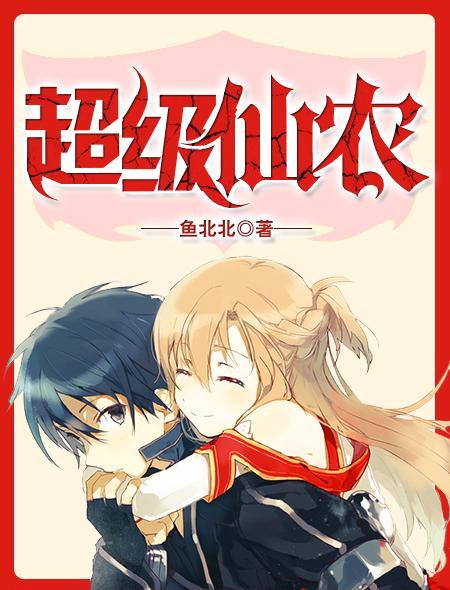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漂亮宝贝和不会爱先生格格党 > 第201章(第2页)
第201章(第2页)
秦濯铁着脸:“再说现在就走。”
“不走,ua!”阮乔踮脚亲上先生的唇。
被软软地包着,秦濯喉结滚动一下。
阮乔弯着眼睛卖乖:“老公好喜欢你呀。”
秦濯身体不自觉绷紧。
先前哄着打着才肯叫一声,现在叫这么甜。
原来只是退退步就能让宝贝儿主动叫老公啊,秦濯心里痒得不行。
体验不错,下次还退。
现在看来,拍这个破精灵好像
也没那么糟心了。
安抚好醋坛先生,阮乔被化妆师领去做造型。
盛晗在旁边监督,忍不住八卦说:“小乔啊,你和秦总感情真好。”
阮乔愣了下,心说秦濯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啊,想到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传开的喊楼事件,尴尬笑了笑。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盛晗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两情相悦的人在一起不是最好的事儿吗?”
阮乔想到秦濯先前冒犯人家的话,找补埋怨说:“好什么呀,他就知道管着我。”
盛晗揶揄地笑了笑,问:“你不喜欢被管着吗?”
阮乔咬了下嘴唇。
“我可是对每一个合作对象都有了解的哦,”盛晗自信地说,“我研究过你不同时期的画。”
同为美的呈现者,盛晗对美术也颇有研究,她认真点评阮乔的作品:“说实话早期就已经很有灵气了,但是风格还不稳定,感觉你那时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就有种呃……拧巴的感觉。”
“但从某个节点之后的画就很和谐了,突飞猛进,”盛晗眨了下眼睛,会心一笑说,“我能看懂。”
化妆师要开始上眼影,阮乔对盛晗笑了笑闭上眼睛。
他知道盛晗说的是什么。
以前徐澜说过,他的画自由,又不自由。
伊恩也说过类似的话。
阮乔一直不明白。
直到在秦濯生日那晚,他接到那个无声的电话。
那时候他对秦濯的感情已经被牢牢封在心底两年,却在那一刻悄然松动。
也许它们本就一直想出来,只是在等一个契机。
那天阮乔完全放空了自己,把自己交给画笔,画出了他的结业作品,也是那一年评分最高的作品。
伊恩说他好像要开窍了。
阮乔后来迷茫了很久,终于注意到自己奇怪的地方。
他从十二岁开始陷在一桩冤案的泥潭里,被误解,被针对,小心翼翼不得自由,所以自由才是他最向往的东西。
可是在他任凭内心想起秦濯的那天,他不仅想到秦濯给他的烟花和创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