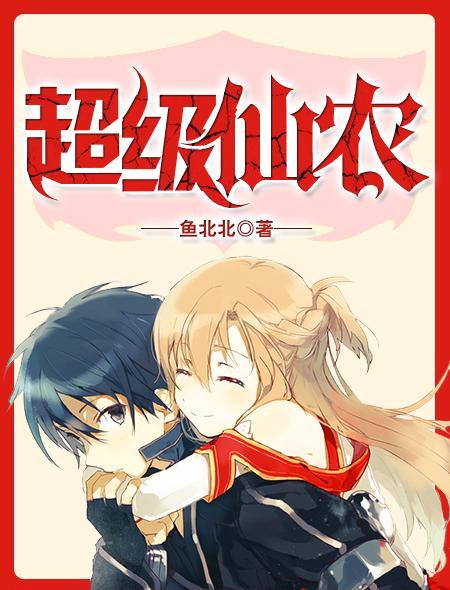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漂亮宝贝和不会爱先生格格党 > 第204章(第2页)
第204章(第2页)
酒红色床单变成一张画纸,落下深浅不一的掌印和抓痕。
秦濯体温高得灼人,什么也浇不灭他此刻内心的炽热。
他的小宝贝回来了,不生气了,真的原谅他了。
阮乔被吻得晕晕乎乎,乖顺地搂住他脖子。
秦濯问:“今天是几号。”
阮乔不好意思地在他脖颈蹭蹭脑袋说:“最大的。”
秦濯咬他耳朵:“给宝贝换个更大的。”
所有的准备和期待在这一刻水到渠成,毛茸茸被丢开,秦濯终于拥有了他的宝贝。
“小狗狗,我的小狗……”低哑的声音咬在阮乔耳朵上。
时隔五年归船入港,刚要搅第一桨池水,秦濯突然感觉到阮乔浑身紧绷。
“怎么了,宝宝。”他停下问。
阮乔正闭眼难受地按着太阳穴,秦濯碰了碰他额头:“宝宝,哪里不舒服?”
阮乔睁开眼,迷离的眼神问:“你是谁啊……”
秦濯心头一僵,连带着其他地方也僵硬,阮乔这下察觉到异样,低头一看顿时发出一声尖叫。
“变态!”
“啪!”
刚实现人生一秒快乐的秦总被宝贝儿抽了个大耳光。
踹下床。
-
陆然赶到时,阮乔正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攥着棒球棒,身上披着小黄鸭毛毯,不知道还以为穿越到了美剧犯罪现场。
“怎么回事啊?”陆然问秦濯。
这一看给他没忍住笑了,高冷威严的秦总脸上好红一巴掌印儿。
前段时候陆然把拳馆从榕城搬到京市,说是兄弟们都在京市,他在老家除了被不停上拳馆的gay塞小卡片寂寞死了。
正筹备着收到秦总的死亡呼叫,一猜和阮乔有关急吼吼就开车过来,这下看见人好生生没事才算放心。
“陆然!”阮乔脆生生叫一嗓子。
陆然过去,阮乔跟不认识他似的来回打量几眼,撇撇嘴说:“你变油了。”
陆然:?
他这晚上跟合伙人吃饭梳的霸总头好吗,上次阮乔看见还夸他沉稳来着。
陆然仔细瞅瞅阮乔神色,这才觉出不对来,又看向秦濯。
秦濯闭了下眼,指指脑子。
“阮阮,陆然你还记得吧,你听他和你说。”
秦濯一开口阮乔就进入防御状态,攥紧棒球棒:“你就站那儿,不要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