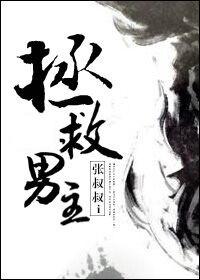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沙德维尔的暗影三部曲顺序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但我现在觉得他说得对。”
福尔摩斯用颤抖的手拿起自己的烟斗。他选了斗更大的樱桃木烟斗,而不是黏土的那只,但当他想往烟斗里填入烟草时,烟叶却撒得到处都是。我不得不替他完成了这个任务,还替他划了火柴。看到原本这么能干的男人,却衰弱得无法做出这最为简单的动作,真让人痛苦。
他抽了几口烟,又恢复了一些元气,这才有了足够的力气,讲述他最近的这场冒险。
*
一开始福尔摩斯以为公孙寿会把他带去石灰屋,但那辆四轮双座马车在马里波恩路朝右转了,没有左转。而后他们又驶过海德公园,此时他觉得公孙寿在贝尔格莱维亚的乡间别墅是他们最有可能的目的地。但这个推测同样错了,马车继续向南,经过那块区域,穿过泰晤士河。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看来他的旅程还长着呢。
在这过程中,公孙寿谈起了自己的事。他提起自己在青海度过的童年,那地方是中国西北部的高原省份,靠近西藏。他的家人都是农民,靠贫瘠的土地勉强挣口饭吃,近乎身无分文。年轻时的公孙寿野心勃勃,梦想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没过多久,在他年长后,便离开家乡,想办法去了北平。
在那儿,他干过不少卑微的工作,从给名声败坏的家庭倒夜壶,到推车上街叫卖饺子和饭团。乡音和方言让他听起来像个乡下人,还常常引人嘲笑,因此他改掉口音。他竭力模仿北京人更精致也更文雅的说话方式,直到他可以冒充他们中的一员。他发掘出了自己仿佛变色龙一般的适应才能。
在首都,他亲眼见证了鸦片贸易是如何蹂躏他的国家。到处都有瘾君子,男男女女都穷得衣衫褴褛,不得不变卖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只为了满足对麻醉品的依赖。从鸦片中获益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他们在印度种植罂粟,然后将它们运到中国;另一种则是本地的掮客,负责将鸦片兜售给中国人。自十七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将丝绸、瓷器和茶叶为主的商品售往全世界,产生了大量对英国的贸易顺差,而东印度公司以这种方式,设法又将它收了回去。鸦片贸易是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是不开一枪就征服一个国家的方式,如此看来,中国最后觉得受够了它,皇帝由此采取行动,没收并销毁了大量鸦片也是毫不奇怪的事。英国以炮舰报复,而这就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公孙寿本人在那时候也做了鸦片掮客,他与东印度公司交易,乘双桅舢板船在海岸边与英国人的商船接头,以白银支付英国人的货物,将它们运回大陆分销。他痛恨鸦片对中国造成的破坏,但他的生存本能告诉他,这就是赚钱之道,暴利消解了他的道德义愤。到二十五岁时,他已经相当富有了。到三十岁时,他成了无可辩驳的富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比同行更无情,售价也比同行更低。他将他的影响力范围逐渐扩展,从北平南下上海,接着到香港和澳门,把所有挡他道的人全都推开。他掌握了流畅的英语,这让他能更好地与英国人交易,对方也因此而更偏爱他,因为他发音清晰,彬彬有礼。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当着他的面,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白的黄种人”,言语之间带着极大的恭维之意。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英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有条款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国家被迫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而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各国势力虎视眈眈,它们有些较为文明,另一些则极为贪婪。对公孙寿来说,他的祖国已经死了。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
“所以你就来到英格兰,”福尔摩斯说道,“熟悉的恶魔比不熟悉的恶魔更好。”
“正是如此,”公孙寿说道,“在中国没有未来。未来在这里,在这些击败了中国的地方。在这里,我过去曾经学到的经验,还有我作为‘最白的黄种人’的身份,都能发挥作用。掌权者容忍了我的存在,即使不请自来,我也会受到招待,有点像是某种上流社会的新玩具,但我不知疲倦地顺利升到了顶层——至少,是我的种族所能达到的顶层。”
“但你对我们始终心怀怨恨。所以你开了鸦片馆。这是你对大英帝国的小小复仇。”
“您能为此而责怪我吗?当我看到一个英国人因鸦片瘾而堕落,因渴望而毁灭,倾尽全部家当,直至除一身衣衫外一无所有,被给我的祖国带来如此多灾难的同一种毒品打倒,难道都不容许我偷偷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公孙寿不再掩饰自己卑劣的行为和卑鄙的动机。伪装示人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
双座四轮马车继续向前,穿过市郊沉睡中的旺兹沃思、温布尔登和莫登,而现在,福尔摩斯推测他们的目的地恐怕是公孙寿在萨里郡的住处。这个中国人在多尔金边缘地带有五十英亩的地产,他那摄政王时期风格的庄园别墅就坐落在“能手”布朗设计的花园群之中。
我的朋友再次猜错了,不过这一次只错了一部分。四轮马车确实在别墅外停下,但只是中途停留片刻而已。福尔摩斯留在座位上,公孙寿则进了门。天边已渐渐亮了起来,带着蒙蒙薄雾。马车夫给他们换了新马。公孙寿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只铁边小箱子,双座四轮马车沿原路返回,再次驶入庄园外的乡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