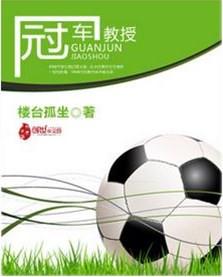帝王小说网>万万不可漫画免费下拉式 > 第158章(第1页)
第158章(第1页)
他说完抬头看了一眼梁焕,发现他整个身子都在抖,神情也难看得很。朱幸不由得疑惑,这个案子怎么引起他这么大的反应?
“那你来找朕,是让朕做什么?”梁焕的话音听不出情绪。
朱幸莫名有些害怕,却还是有一说一:“四品官员判革职,按例要上报。黄湖此人,臣不好报给两位丞相……”
“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黄湖,其他人就这么判了是吗?你判斩四个人,朕管不着是吗?”
汗水从双鬓滑落,朱幸心中一沉。他这么多年战战兢兢地在两位丞相之间周旋,才换来如今的地位。但如果这位正主儿对他不满,那他可就白忙活了。
于是他露出个谄媚却难看的笑,“自然是听您安排。您若想保谁,臣就改改试试……”
这时卢隐进屋,叫了声:“陛下,打听到了。”朱幸在这里,他不确定后面的话能不能说。
“不用了,出去吧。”梁焕淡淡道。
他起身在屋子里踱了一圈,突然站定看着他,质问道:“那些暴民呢?为什么不清算他们的罪过?”
朱幸小心地回答:“百余人都在江州关着。目前刑部主张把罪过算在官员头上,若将责任推给暴民,那这些官员倒是可以都轻判或不判。”
“行了,拖着吧。”梁焕别过头道。
“拖着?”
“拖着不会吗?还用朕教你怎么拖着?”
朱幸唯恐他动怒,连连点头,“是,臣知道了,回去让他们慢慢审理。”
“还有,”梁焕严肃地命令道,“刑部大牢里的人,你都要看好了。不许病了,更不许死了!”
朱幸回去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这件远在江州的案子,到底哪里触动了梁焕,让他如此上心。
第二天早朝后,林烛晖跟着梁焕进了未央宫。梁焕也正打算找他,开口便问:“江州的案子你听说了吧,有什么办法么?”
然而林烛晖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想的:“陛下,您可能不知道,早年间黄湖这个人曾代表欧阳党叱咤风云,后来不折腾了,手里却一直握着他们的人脉。还有江州那个州同,借着掌管钱粮的名义,在临近几个州都有关系,将南边握得死死的。”
“收拾了这两人,他们几乎就没什么势力了。臣去问了刑部的判决,臣以为对黄湖可以再重一些……”
梁焕冷冷地打断他:“刑部跟朕说,要判刑,那就是所有人一起判。”
林烛晖愣了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轻叹口气,缓缓道:“这件事了结,欧阳党便是苟延残喘了。陛下,大局为重。”
梁焕浑身的骨肉都紧绷着,他一直以为自己敬爱的老臣对自己也是十分照顾,从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没有回应林烛晖。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强烈的情绪冲垮了理智,让他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