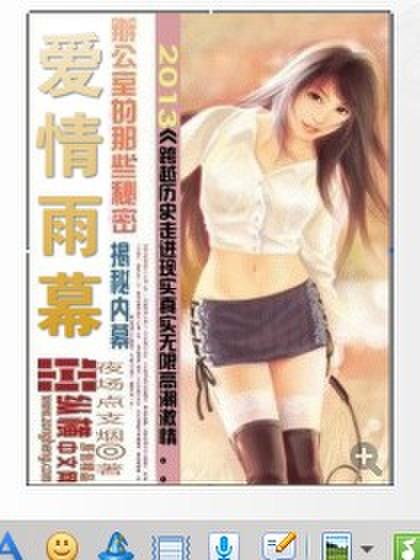《爱情雨免费》第二十六章 茶
资格和她说话;而在这里,却对着一盆脏衣服居高临下质问她。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会给他一个说法。” 余素芬和我一起做菜,身上的领导气质又回来了:肉丝切多细,姜放多少,水淀粉勾多厚,菜什么时候下锅,都是她说了算,尽管菜做出来后,我并没发现有太大了不起。但她去哄陆丰起来吃饭时,又像是一个做错事情、不知所措的小孩。我忽然明白了陆丰何以会对她难以割舍:一个在外人面前斩钉截铁、呼风唤雨的女人,偏偏在你面前放下身段,温顺听话,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杀伤力。 女人,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 下一个周末,余素芬请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饭,大约有“谢罪”的意思。她专门下厨,比较特别的是,她亲手做了一个蛋糕。 等她走了,陆丰把吃剩的小半个放进冰箱,...
《爱情雨免费》最新章节
- 第二十六章 茶
- 第二十五章 专门下厨
- 第二十四章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 第二十三章 情义
- 第二十二章 一克拉的钻戒
- 第二十一章 五马街
- 第二十章 黑巧克力
- 第十九章 一定要结婚才能住在一起吗
- 第十八章 惊艳
- 第十七章 BOSS包包
- 第十六章 知情就报多煞风景
- 第十五章 薄荷摩卡味道
《爱情雨免费》章节列表
- 第一章 远离故乡
- 第二章 我们还会在见面吗
- 第三章 雁荡山的夏季
- 第四章 新年礼物
- 第五章 告别处男时代
- 第六章 精心包扎过的礼物
- 第七章 夺人所爱
- 第八章 情绪戒指
- 第九章 塑胶旧凉鞋
- 第十章 爱情真他妈的是个王八蛋
- 第十一章 尘封的回忆
- 第十二章 江心屿大桥
- 第十三章 如假包换王八蛋
- 第十四章 泪光
- 第十五章 薄荷摩卡味道
- 第十六章 知情就报多煞风景
- 第十七章 BOSS包包
- 第十八章 惊艳
- 第十九章 一定要结婚才能住在一起吗
- 第二十章 黑巧克力
- 第二十一章 五马街
- 第二十二章 一克拉的钻戒
- 第二十三章 情义
- 第二十四章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 第二十五章 专门下厨
- 第二十六章 茶